美國向來是鼓勵和標榜多元化的國家,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碰撞和交融,使得美國成為(wei) 一個(ge) 種族大熔爐。那麽(me) ,事實果真如此嗎?本文作者Beth Nguyen作為(wei) 一名從(cong) 小生長在密歇根州的越南裔,她的越南名字曾讓她十分困擾,但周圍的很多美國白人都告訴她,這個(ge) 名字很酷。異國情調對美國白人來說很“酷”,但“貢獻”這份異國情調的人又經曆了什麽(me) 呢?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本文於(yu) 2021年4月發布在《紐約客》雜誌上。
大家總是讓我不要改名字。有些人堅持說他們(men) 喜歡這個(ge) 名字,Bich。我出生在越南西貢,Bich(發音為(wei) Bic)是一個(ge) 普通的越南名字。當家人給我起名字的時候,他們(men) 並不知道八個(ge) 月後我們(men) 會(hui) 成為(wei) 難民,也不知道我會(hui) 在20世紀80年代的密歇根州長大,那是一個(ge) 保守的白人州,那裏的女孩都叫Jennifer、Amy和Stacy這樣的名字。
像Bich這樣的名字不僅(jin) 讓我“脫穎而出”,還讓我可悲地成為(wei) 眾(zhong) 人矚目的焦點。大家會(hui) 問,“你叫什麽(me) ?”有些人會(hui) 當麵嘲笑我,“你知道你的名字是什麽(me) 意思吧?真的是你父母給你起的嗎?”
我一直很羨慕其他的亞(ya) 洲孩子,他們(men) 的父母允許他們(men) 改名字,或者單獨給他們(men) 起一個(ge) 美國名字。本命叫Phuoc的人在學校就叫Phil。但我的父母不讓我改名,他們(men) 說我應該為(wei) 自己感到驕傲。我隻能把擔憂留給自己,因為(wei) 我不想拋棄我家的越南文化,所以我選擇了不改名。
點名時的緊張是我對學校最早的記憶,我總是試圖搶在老師點名之前報上自己的名字,以免尷尬。善良的老師會(hui) 直接問我名字該怎麽(me) 叫,在幾乎全都是白人孩子的班級裏,不難想到誰會(hui) 叫Bich。我小時候的性格就十分害羞,後來因為(wei) 不想提到自己的名字,變得更加害羞。我時常為(wei) 自己沒有足夠的膽量來承受美國人的凝視和嘲笑而感到羞愧。
名字既是私人的,也是公開的。我們(men) 很難避免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一些公開的場合:表格、文章、郵件……在每一份小學作業(ye) 的頂部,其他孩子會(hui) 用星星或愛心貼紙來裝飾自己的名字,試圖讓自己的名字看起來比別人的更大,光是看到名字本身就會(hui) 讓他們(men) 感到開心和滿足。我從(cong) 未感受過這種快樂(le) ,一次也沒有。對我來說,我的名字是一種嘲弄,我一直努力不去看它。
Bich這個(ge) 單詞的意思是翡翠。大多數聲稱喜歡“Bich”這個(ge) 名字的人,或者對改名這個(ge) 想法感到憤怒或恐懼的人,都是白人女性。是她們(men) 告訴我這個(ge) 名字很酷,很有趣,很獨特,是我的文化遺產(chan) 和文化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她們(men) 說,她們(men) 很喜歡我的名字,如果我改了,她們(men) 會(hui) 很傷(shang) 心的。她們(men) 沒有說她們(men) 希望擁有這個(ge) 名字。我想相信她們(men)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選擇了相信她們(men) 。但我也知道,她們(men) 喜歡是因為(wei) 她們(men) 不必麵對這背後的複雜。她們(men) 喜歡異國情調,並沒有去想,異國情調隻有利於(yu) 那些定義(yi) 什麽(me) 是異國情調的人。有時我在想他們(men) 是否也“喜歡”為(wei) 我感到難過。
我一直試圖適應Bich這個(ge) 名字。過去我常常在“i”上麵加聲調以表示正確的發音:Bích。這個(ge) 聲調介於(yu) 問號和感歎號之間。但我怎樣才能擺脫凝視呢?過去的經曆讓我這個(ge) 名字打上了恥辱的烙印,因為(wei) 作為(wei) 難民和難民的孩子在美國生活本身就是恥辱。
我無法將Bich這個(ge) 名字從(cong) 我的童年剝離出來,也無法將它從(cong) 別人嘲笑我、辱罵我的經曆中剝離出來,它讓我感覺到我自己就是個(ge) 笑話,而我卻因為(wei) 太愚笨或太害怕,什麽(me) 都不能做。當我看到由這幾個(ge) 字母拚出來的名字時,我看到的是一個(ge) 想要躲避創傷(shang) 的自己。即使是當下在打字的時候,我也很想轉身離開。美國摧毀了我的名字,我也讓它這麽(me) 做了。
寫(xie) 到關(guan) 於(yu) 我名字的故事,就不得不寫(xie) 到種族主義(yi) ,寫(xie) 到種族主義(yi) 就不得不寫(xie) 到暴力。我記得,小時候聽到爸爸和叔叔們(men) 在竊竊私語關(guan) 於(yu) 文森特·陳在底特律被謀殺的事。今天,我和我的孩子們(men) 談論亞(ya) 特蘭(lan) 大六名亞(ya) 裔女性被殺害的事情。我告訴他們(men) 什麽(me) 是殖民主義(yi) 、東(dong) 方主義(yi) 和反亞(ya) 洲移民法。我告訴他們(men) 當亞(ya) 裔群體(ti) 被忽視時會(hui) 發生什麽(me) ——成為(wei) 製造恐懼,強製服從(cong) 和激化種族主義(yi) 的方式。我和孩子們(men) 為(wei) 此擔心了很多年。這些天,我們(men) 出門的時候都格外小心。
(*文森特·陳,指陳果仁,是一名美籍華裔製圖員,1982年6月19日在密歇根州韋恩縣被兩(liang) 名白人毆打致死。行凶者對當時汽車行業(ye) 居高不下的失業(ye) 率感到不滿,並將此歸咎於(yu) 日本汽車工業(ye) 的成功。這樁謀殺案被視為(wei) 底特律汽車工業(ye) 工人對亞(ya) 裔的仇視和敵對情緒的縮影。)
然而,在我的生命中,美國一直告訴我,是我反應過度了。嘲笑亞(ya) 洲人的名字是可以的,嘲弄亞(ya) 洲人也是ok的——那些外國人長得都一樣,口音滑稽又難聽,它不斷地發生在媒體(ti) 和現實生活中。當它發生時,亞(ya) 洲人對此表示憤怒,他們(men) 會(hui) 反駁說,“你太敏感了,這隻是個(ge) 玩笑。”是啊,這個(ge) 笑話比我們(men) 的存在更重要。
我的姓氏Nguyen是最常見的越南姓氏,在美國,它已經從(cong) “令人生疑、難以發音的外語”變成了“可接受的不同語言,隻是有些難發音”。Bich還在等待屬於(yu) 它的機會(hui) 。改名是戰略性的、安全的、自我關(guan) 懷的(行為(wei) )嗎?這麽(me) 多年來我一直想弄明白,想把它寫(xie) 下來。我所知道的是,作為(wei) Bich,在80年代一個(ge) 白人居多的小鎮長大,就像是一個(ge) 總是失敗的測試。這是一種雙重約束:那些讓我對自己名字感到不舒服的人,會(hui) 認為(wei) 我改名就是背叛自己的傳(chuan) 統,而我一直想要的無名無姓,不受凝視,是不可能的。
我總是在餐館使用假名,比如Rose、Sophia或Beatrice。幾年前的一天,我在麥迪遜廣場公園的Shake Shack,櫃台後的女人幫我點單,問了那個(ge) “可怕的問題”,我說:“Beth”。她點點頭,沒有懷疑我的答案。在那一刻,我感覺很真實,我不隻是在說“Beth”這個(ge) 名字——我就是Beth。所以我開始用這個(ge) 名字,向銷售人員,向保姆、電工、新朋友、新同事。我會(hui) 說Beth,然後一個(ge) 小小的快樂(le) 的衝(chong) 擊波會(hui) 臨(lin) 到我,就像炎熱的天氣從(cong) 冰箱裏冒出來的冷空氣。就像一個(ge) 秘密,就像另一種生活。
Beth是一個(ge) 社會(hui) 實驗,來驗證有一個(ge) 好讀的名字在美國生活會(hui) 更容易,而事實的確如此。當我的名字叫Beth時,我看起來更像美國人而不是亞(ya) 洲人。經曆過兩(liang) 種名字帶來的不同待遇,既是有啟發的,也是痛苦的。作為(wei) Bich,我是一個(ge) 讓人不舒服的外國人。可作為(wei) Beth,我的英語從(cong) 來沒有被稱讚過。
我最親(qin) 密的朋友自然地接受了這個(ge) 名字。其他人則表示驚訝和不讚成。有些人告訴我,他們(men) 都會(hui) 繼續喊我原來的名字。我好像明白了。但是,如果你拒絕接受別人為(wei) 自己起的名字,不就是拒絕接受這個(ge) 人,或者拒絕他為(wei) 自己做的選擇嗎?我選擇成為(wei) Beth,讓我過得更輕鬆的Beth,而不是成為(wei) 讓別人活得更輕鬆的Beth。
盡管如此,因為(wei) 我還沒有在法律上改名,我所有文件上的名字仍然是Bich。有一次,我和孩子在商店裏,向店員出示我的駕照。她笑了起來,“這真的是你的名字嗎?”她問道。以前的我為(wei) 了避免尷尬可能會(hui) 跟著笑,不好意思地說,“是啊,這個(ge) 名字很難發音。”但是我的孩子跟我在一起,我就一直盯著這個(ge) 女人,直到她覺得尷尬為(wei) 止。我們(men) 離開的時候,孩子對我說,“剛才那個(ge) 女士在嘲笑你的名字,這很刻薄。”我想這是他第一次經曆這樣的事情,因為(wei) 他和他的兄弟都有一個(ge) 簡單而直接的名字。
最近,孩子們(men) 在學習(xi) 古代語言,學習(xi) 單詞和發音是如何演變的。我告訴孩子們(men) ,有時候這種轉變非常緩慢,以至於(yu) 一次隻能被識別出一點點。我們(men) 也是這種轉變中的一部分,比如俚語、俗語、新單詞、新的發音。單詞不會(hui) 自己改變,但我們(men) 的認知需要改變。
現在,Beth就是我的轉變。這種轉變是令人感到舒服的。它不會(hui) 改變我的過去、我的家庭、我們(men) 在美國的難民生活。它也不會(hui) 是永遠的。這感覺像是一個(ge) 空間,在這個(ge) 空間裏我能決(jue) 定自己以何種方式被看到,而不是被別人決(jue) 定。我意識到,我這一生都在等待著某種許可,就是我允許自己成為(wei) 這樣的人的許可。
文章發表後引發了大批亞(ya) 裔網友的關(guan) 注和討論,大家紛紛在評論區留下了自己的觀點和分享。
SifficientTill3399:作者的經曆和我非常像,我一直承受著名字帶來的創傷(shang) 。我媽媽對印度文化感到癡迷,因為(wei) 她自己在八歲就離開了印度,所以對純梵文的名字很癡迷。結果,她給我起了個(ge) 很女性化的名字,讓我成為(wei) 了校霸的靶子。
我很想擺脫這個(ge) 名字但她多年來一直拒絕,她認為(wei) 這是對霸淩者的屈服,隻是一心想在我身上留下印度文化的標記。我13歲改名那天,她非常難過,因為(wei) 她一直把我看作是實現她某種幻想的方式,幻想著在保留印度文化的同時選擇性地融入美國文化。
已注銷:想想那些美國人是怎麽(me) 讀“Wang”的,每次他們(men) 發出“Wayyyyyng”的聲音我都要瘋。
cecikierk:我有個(ge) 非常典型的亞(ya) 洲名字。我看到過一個(ge) 帖子,帖子裏麵我的名字在中國人那裏是當作辱罵的詞來用的。我不會(hui) 改名,但這真的很不好受。
th30be:這絕對不是隻有美國才會(hui) 出現的問題。這隻是語言的問題。作者說的情況會(hui) 發生在任何說英語的國家。
crayencour: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帝國主義(yi) /殖民主義(yi) 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國家等級製度。美國人會(hui) 為(wei) 了搞清楚法語單詞的正確發音而自找麻煩,同時取笑亞(ya) 洲/非洲名字。問題的根源在於(yu) 美國人對歐洲高雅文化的崇拜和對其他文化的歧視和蔑視。
如果他們(men) 真的尊重你,他們(men) 就會(hui) 學習(xi) 讀你的名字。
對此,你怎麽(me) 看?究竟是美國白人太傲慢了,還是作者反應過度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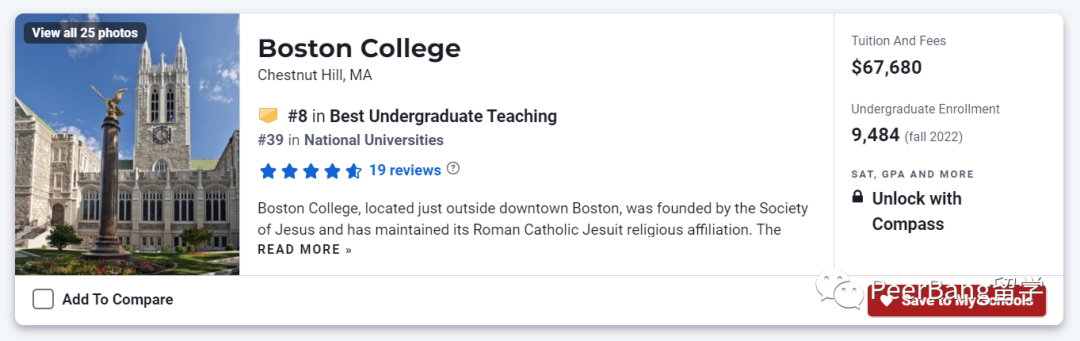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