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TASS(全名:Telluride Association Summer Seminars;原名TASP)被公認為(wei) 人文領域的頂級夏校,以其高含金量和高選拔性著稱,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最難申請的人文類夏校。
24屆的TASS項目即將於(yu) 2024年1月4日截止,近日在協助學生準備TASS申請的時候,老師看到一篇關(guan) 於(yu) 22夏季TASS項目的博客,其內(nei) 容是一名黑人教授講述自己在該項目授課時被學生認為(wei) 是種族主義(yi) 者,最終該課程因為(wei) 政治爭(zheng) 議問題被迫提前停止。
想來有意向申請TASS的同學應該對此類話題頗有興(xing) 趣,故編譯了這位教授的原文供大家思考學習(xi) 。
作者信息
姓名:Vincent Lloyd
美國維拉諾瓦大學教授
政治神學研究中心主任
《Black Dignity: The Struggle Against Domination》作者

▲原標題:一位黑人教授,被困在反種族歧視者的地獄裏。原文發表於(yu) 2023年2月10日。
研討會(hui) (Seminar)第一天時陽光明媚,我和一群緊張而興(xing) 奮的17歲少年們(men) 坐在野餐桌邊。12名高中生被泰留瑞德協會(hui) (Telluride Association)通過嚴(yan) 格的申請程序選拔出來(據報道錄取率約為(wei) 3%)一起參加為(wei) 期六周的大學級別的課程,該項目所有費用都已由協會(hui) 承擔。
這個(ge) 團體(ti) 讓我想起了我給女兒(er) 讀的《本尼迪特天才秘社》書(shu) 中的英雄:在這些為(wei) 了一個(ge) 共同的項目而聚集在一起的青少年之中,每個(ge) 人都有非凡的能力和一些怪癖。一個(ge) 來自加州的女孩以機關(guan) 槍一般的速度說話和思考,並在疫情期間開始收集寵物蝸牛,現在她有100多隻蝸牛了。一個(ge) 來自中國省立學校的女孩雖然從(cong) 未去過美國,卻掌握了不帶口音的英語,並非常熱愛E.M. Forster的作品。除了參與(yu) 研討會(hui) ,學生們(men) 還實行民主自治:他們(men) 住在一起,並且製定自己的規則。在最初的幾天,學生們(men) 正如所期待的那樣,時而活潑,時而拘謹,所有人都好奇、有趣,嚐試與(yu) 他人、與(yu) 研討會(hui) 的內(nei) 容建立聯係。
四周後,我再次坐在聚集的學生們(men) 麵前。現在,他們(men) 的表情冷漠,眼睛無神。從(cong) 第一周開始,我沒有再看到一個(ge) 人的微笑。他們(men) 的人數減少了兩(liang) 個(ge) :前一周,他們(men) 投票將兩(liang) 個(ge) 同學趕出了研討會(hui) 。而我將是下一個(ge) 。
每個(ge) 學生都讀了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聲明,內(nei) 容是關(guan) 於(yu) 研討會(hui) 如何在內(nei) 容和形式上延續了針對黑人的暴力、黑人學生如何受到傷(shang) 害、我如何對無數次微小的侵犯負有罪責(包括通過我的肢體(ti) 語言),以及學生如何因為(wei) 我沒有立即糾正那些未能將歧視黑人視為(wei) 世界所有問題的原因的觀點而感到不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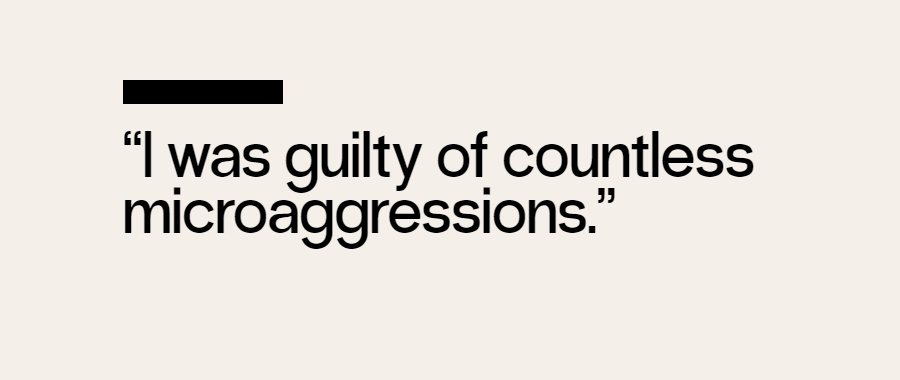
這可能隻是對校園“覺醒”文化和傳(chuan) 統教育美德喪(sang) 失的又一次哀歎。然而,我們(men) 的研討會(hui) 主題是“美國的種族和法律界限”。我們(men) 6周的研討會(hui) 中,有4周的主題是關(guan) 於(yu) 反黑人的種族主義(yi) (另外兩(liang) 周則在關(guan) 注反移民和反原住民的種族主義(yi) )。我是一名黑人教授,主管我大學的黑人研究項目,領導著反對種族主義(yi) 和倡導轉型正義(yi) 的工作坊,出版了關(guan) 於(yu) 反黑人種族主義(yi) 和廢除監獄的書(shu) 籍。我住在費城一個(ge) 以黑人為(wei) 主的社區,我的女兒(er) 在一所以非裔文化為(wei) 中心的學校上學,另外我是當地黑人文化組織的董事會(hui) 成員之一。
像其他左翼人士一樣,我曾經對針對當前美國對種族問題討論的批評不屑一顧。但現在,我的思緒轉到了1970年代的那個(ge) 時刻,當時左翼組織崩潰了,對匹配和提高自己同誌的戰鬥性的需要導致了一種充滿教條主義(yi) 和幻滅感的有毒文化。一群精神煥發的高中生怎麽(me) 也會(hui) 這樣?

泰留瑞德協會(hui) (Telluride Association)常年來一直保持低調,即使在高等教育界也是如此,但它在塑造美國精英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它的校友有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酷兒(er) 理論家Eve Sedgewick和後殖民理論家Gayatri Spivak(為(wei) 協會(hui) 第一位女性成員)、佐治亞(ya) 州政治家Stacey Abrams和記者Walter Isaacson、新保守派的Paul Wolfowitz和Francis Fukuyama(其曾在協會(hui) 的董事會(hui) 任職)。1911年,礦業(ye) 企業(ye) 家L.L. Nunn在創建深泉學院的幾年前創辦了這一協會(hui) ,它的目標是在高中生和大學生中培養(yang) 民主的社群。它在康奈爾大學和密歇根大學附近有學術基地,學生在這裏獲得獎學金,實行自治,並將學術生活和服務性工作融入他們(men) 自己的集體(ti) 生活。1954年,泰留瑞德協會(hui) 開始了它的高中生暑期項目。
多年來,許多美國頂尖大學的教師都曾為(wei) 該項目授課。課程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共產(chan) 主義(yi) 和民主製度的理念衝(chong) 突”是在1956年講授的;哲學家Robert Nozick在1965年講授了“自由的哲學概念”,而最近幾年的主題包括“凱爾特人和維京人的神和英雄”、“數字世界中的公共詩歌”、“安全國家的文學”和“自由之夏”。
2014年,我在泰留瑞德的康奈爾校區教過“種族和法律的界限”。最初的幾天和我在2022年研討會(hui) 一模一樣:學生們(men) 都擁有著過人的能力;他們(men) 會(hui) 問一些試探性的問題;他們(men) 有時也會(hui) 很尷尬。然後,隨著六個(ge) 星期的過去,我可以看到學生們(men) 彼此之間以及與(yu) 我之間形成了紐帶,我可以看到他們(men) 對課程的付出與(yu) 努力。他們(men) 總是準時出現並完成好作業(ye) 。研討會(hui) 期間,我女兒(er) 剛滿1歲,由於(yu) 我們(men) 在鎮上誰也不認識,我們(men) 還邀請了學生們(men) 到我們(men) 住的房子裏參加她的生日聚會(hui) 。
六年後,我偶然發現了泰留瑞德的網站,並驚訝地在首頁看到了我在生日聚會(hui) 上的照片。帶著這些美好的回憶——以及由於(yu) 在全美國的相關(guan) 討論因為(wei)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而發生如此大的變化之後,重新探討有關(guan) 種族的棘手問題的可能性讓我興(xing) 奮不已——我聯係了泰留瑞德,希望再次教授這個(ge) 研討會(hui) 。(協會(hui) 的研討會(hui) 是共同講授的,我的研討會(hui) 是和我妻子合作開設的,她是一名律師同時也是原住民研究的教授。)
在George Floyd之死引發的抗議之後,一群黑人校友向泰留瑞德協會(hui) 施壓,要求檢討種族主義(yi) ——他們(men) 聲稱,種族主義(yi) 已經融入了協會(hui) 的文化。他們(men) 的公開信說:“我們(men) 都經曆了協會(hui) 內(nei) 部和其項目中對黑人的歧視”。結果,夏季的研討會(hui) 項目被重新設計:現在隻提供“批判性黑人研究”和“反壓迫研究”的研討會(hui) 。前者將“尋求更具體(ti) 地關(guan) 注黑人學生的需求和興(xing) 趣。”而我的研討會(hui) “種族和法律的界限”屬於(yu) 後者的研究範疇。
泰留瑞德項目在演變的過程中延續了其追尋自由價(jia) 值觀的傳(chuan) 統。它從(cong) 1950年代就已開始提供種族相關(guan) 的課程,其康奈爾校區在1970年代被稱為(wei) “校園中最自由的小群體(ti) ”,因為(wei) 它相對較早地接受了猶太人、黑人和女性學生。1993年,在美國多元文化主義(yi) 的鼎盛時期,協會(hui) 開始提供一係列新的研討會(hui) ,重點關(guan) 注種族和差異,麵向未被充分代表的學生。但是我的Telluride研討會(hui) 內(nei) 部分歧導致的最終破裂正表明了,這種圍繞黑人性(blackness)展開的、不斷誘惑著美國精英階層(尤其是精英教育機構)的在平權征程上的最後一步,我們(men) 走得太快了,甚至是走入了缺乏條理的自相矛盾,或更糟糕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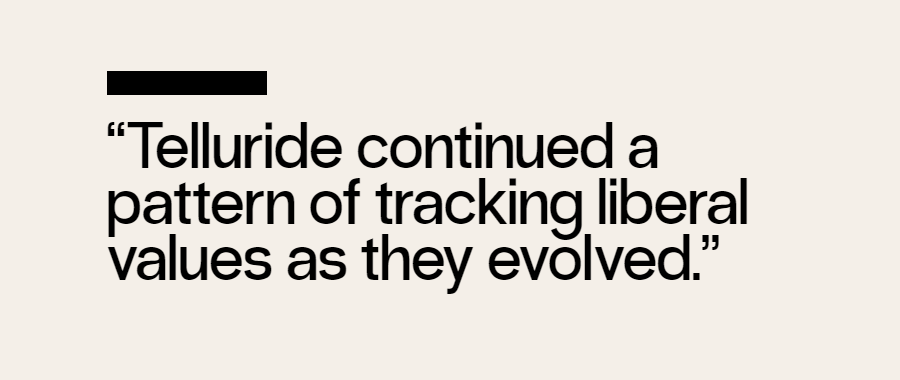
在康奈爾校區,學生們(men) 住在同一棟房子裏,並同時參加兩(liang) 個(ge) 不同的研討會(hui) 。2014年,兩(liang) 個(ge) 研討會(hui) 小組的參與(yu) 者在研討會(hui) 之外共同生活,探索伊薩卡鎮和康奈爾大學的校園,一起吃飯和歡笑,並建立了一個(ge) 係統來共同治理他們(men) 的集體(ti) 。然而,在2022年,我被告知“批判性黑人研究”的學生將單獨生活和學習(xi) ,以創造一個(ge) 完全的“黑人空間”。我的“反壓迫研究”學生和他們(men) 分開了。和我預想的32名高中生一起學習(xi) 生活不同,我的小組僅(jin) 由12名學生組成(在“嘩變”後減少到9人)。
此外,在2022年的項目中,下午和晚上將不再用於(yu) 娛樂(le) 和做作業(ye) 。兩(liang) 個(ge) 大學生被稱做“家務總管”並被分配去創辦反種族主義(yi) 工作坊(Workshop),以填補下午的時間(其中一名領導的人將被我叫做Keisha)。這些Workshop有關(guan) 於(yu) 白人至上主義(yi) 、特權、非洲獨立運動、Angela Davis思想和行動等。所有這些都是在最開始為(wei) 期一天的“轉型正義(yi) ”Workshop之後舉(ju) 行的。這些Workshop迫使高中生麵對棘手的問題,並以他們(men) 從(cong) 未被挑戰過的方式接受挑戰,最終使這些學生們(men) 身心俱疲。
我對反種族主義(yi) Workshop並不陌生,我參加過許多這樣的活動,我自己也主持過這類活動。但是這裏的Workshop是由兩(liang) 個(ge) 大學生組織的,充滿了時代精神。從(cong) 我收集到的信息來看,無論這些Workshop表麵上是關(guan) 於(yu) 什麽(me) 主題,它們(men) 涉及到粗糙地傳(chuan) 達某些教條式的主張:
●經曆苦難傳(chuan) 達著權威。
●壓迫沒有等級之分——除了針對黑人的壓迫,它自成一類。
●相信黑人女性。
●監獄永遠不是答案。
●黑人需要“黑人的空間”。
●聯盟通常是行動性的。
●所有非黑人,還有很多黑人本身,都有反黑人的罪責。
●沒有辦法避免對黑人的歧視。
研討會(hui) (Seminar)的形式與(yu) 反種族主義(yi) 工作坊(Workshop)的形式相反,協會(hui) 試圖同時擁有這兩(liang) 種形式。從(cong) 本質上講,研討會(hui) 需要耐心。日複一日,每個(ge) 發言在另一個(ge) 發言基礎上繼續拓展,因為(wei) 一個(ge) 學生會(hui) 注意到另一個(ge) 學生忽略的東(dong) 西,同時教授會(hui) 將討論引向最重要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基於(yu) 文本:文本中的特定單詞、短語、論點和圖像為(wei) 對話提供了必要的爭(zheng) 議之處,讓參與(yu) 者能夠討論具體(ti) 的事情。導師將會(hui) 溫和地(理想情況下,應該是幾乎看不見地)引導討論向重要的方向發展。
研討會(hui) 假設每個(ge) 學生都有天賦,即使我們(men) 來自不同的背景,擁有不同數量和種類的知識,以及不同的技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我們(men) 利用我們(men) 不同的洞察力一次又一次地互相推動著討論前進,我們(men) 每個(ge) 人最終都會(hui) 達到最好的狀態。當這種實踐是由精心選擇的文本(不僅(jin) 僅(jin) 是“偉(wei) 大的書(shu) 籍”,而是那些在探索至關(guan) 重要的問題時能夠挑戰我們(men) 的文本)引起時,研討會(hui) 就成功了。
這需要時間。第一天,你會(hui) 很沮喪(sang) 。第二天和第三天,你會(hui) 很沮喪(sang) 。即使在最後一天,你也會(hui) 感到沮喪(sang) ,盡管理想情況下,你的沮喪(sang) 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研討會(hui) 上的每一次幹預發言都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會(hui) 把事情搞砸。後來的每一次也會(hui) 是不完整的,也依然會(hui) 出錯。但是這個(ge) 過程中會(hui) 迸發很多見解和驚喜,因為(wei) 每個(ge) 參與(yu) 者用會(hui) 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文本。
我很想加上一句:這就是生活。這就是民主生活。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有不同的、片麵的知識。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會(hui) 一次又一次地犯錯。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men) 通過相互傾(qing) 聽、補充和挑戰同伴的見解來加入這場辯論。在這個(ge) 過程中,幾年來,幾十年來,我們(men) 共同的方向是正義(yi) 和真理。
如果說研討會(hui) (Seminar)是慢餐,那麽(me) 由大學生舉(ju) 辦的反種族主義(yi) 工作坊(Workshop)則像是進食含糖食物過多後的興(xing) 奮。在一個(ge) 具有權威性的場所,所有的標簽都濃縮、打包和傳(chuan) 遞。最糟糕的反種族主義(yi) Workshop隻是為(wei) 參與(yu) 者提供了一種新的回應方式——大聲轉發。

泰留瑞德的學生體(ti) 驗了兩(liang) 種與(yu) 同伴一起學習(xi) 的方式,也體(ti) 驗了兩(liang) 種不同的文化。從(cong) 最初的“轉型正義(yi) ”工作坊(Workshop)開始,學生們(men) 學會(hui) 了在同意同學的話時打響指。這種做法立即進入了研討會(hui) (Seminar),並且被武器化。一個(ge) 學生會(hui) 嚐試發表一個(ge) 有爭(zheng) 議的,或者隻是不尋常的觀點。沉默。然後另一個(ge) 學生會(hui) 重複一條反種族主義(yi) 的教條,房間裏就會(hui) 充滿打響指的聲音。
在2014年研討會(hui) 的第一周,針對奴隸製話題,一名華裔美國學生指出了我們(men) 課文中白人奴隸主為(wei) 被奴役者提供食物的一個(ge) 時期,並表示這表明奴隸製的兩(liang) 麵性。在我想辦法把他的發言變成更複雜的討論的墊腳石之前,兩(liang) 個(ge) 學生提出了文本中的其他證據,表明奴隸製是一種道德上令人憎惡的東(dong) 西,並不值得進行兩(liang) 麵性討論。最初的那位學生,一開始看起來他似乎有種搖擺不定的道德標準,而在研討會(hui) 結束時,他表達了一種新的對待正義(yi) 的信仰。
在2022年的反種族主義(yi) 工作坊(Workshop)上,非黑人學生知道他們(men) 需要以黑人的聲音為(wei) 中心——並且學會(hui) 閉嘴。Keisha報告說,這對亞(ya) 裔美國人學生來說尤其困難,但他們(men) 正在努力。(最終,兩(liang) 名亞(ya) 裔美國學生被開除出這個(ge) 項目,而其原因Keisha說不能告訴我。)這對研討會(hui) 的影響是迅速而顯著的。在第一周,參與(yu) 情況如你所料:有兩(liang) 三個(ge) 害羞的學生隻在搭檔或小組活動中發言,兩(liang) 三個(ge) 直言不諱的學生表達著自己的觀點,其餘(yu) 的則介於(yu) 兩(liang) 者之間。黑人學生一個(ge) 直言不諱,一個(ge) 居中,一個(ge) 靦腆。到了研討會(hui) 的第二周,兩(liang) 個(ge) 白人學生在實際意義(yi) 上沉默了。亞(ya) 裔學生中有兩(liang) 人仍然活躍(正是即將被開除的兩(liang) 人),但絕大多數發言來自三名黑人學生。兩(liang) 個(ge) 酷兒(er) (Queer)學生(一個(ge) 亞(ya) 裔、一個(ge) 白人)完全沉默。黑人學生基於(yu) 自身和其家庭的經曆,有很多的有趣的想法想要表達,但當多種觀點相互碰撞、相互鬥爭(zheng) 並發展時,研討會(hui) (Seminar)才是成功的——而這在這期項目中變得不可能了。
在他們(men) 的“轉型正義(yi) ”工作坊(Workshop)上,我的學生們(men) 學會(hui) 了關(guan) 於(yu) “harms”(傷(shang) 害)的理論。這個(ge) 名詞,以及它所表達的思想框架,來自於(yu) 廢除監獄運動。其支持者鼓勵我們(men) 思考傷(shang) 害以及如何糾正傷(shang) 害,而不是將罪行與(yu) 懲罰相匹配。他們(men) 通常通過邀請更廣泛的群體(ti) 參與(yu) 來辨別傷(shang) 害的影響、產(chan) 生傷(shang) 害的原因以及未來前進的道路。在反種族主義(yi) Workshop的討論中,傷(shang) 害是指任何讓你感覺不太對勁的事情。對於(yu) 一個(ge) 17歲的人來說,在一個(ge) 高度選拔性的、費用已被免除的夏季項目中,新學習(xi) 了“傷(shang) 害”這種概念,可實踐這種理論框架的場景是相對較少的。我的研討會(hui) 成了試驗和武器化這個(ge) 名詞的場所。
在我們(men) 討論監禁時,一名亞(ya) 裔美國人學生引用了聯邦囚犯的人口統計數據:大約60%的被監禁者是白人。黑人學生說他們(men) 受到了傷(shang) 害。他們(men) 在一次Workshop上了解到,“客觀事實”是白人至上主義(yi) 的工具。我被告知,在研討會(hui) (Seminar)之外,黑人學生不得不花大量時間糾正他們(men) 因聽到與(yu) 黑人無關(guan) 的監獄統計數據而受到的傷(shang) 害。幾天後,這名亞(ya) 裔學生被該項目開除。類似地,在進行了一周關(guan) 於(yu) 美國原住民遭受的可怕暴力、死亡和剝奪的討論後,Keisha向我報告說,黑人學生和他們(men) 的盟友受到了傷(shang) 害,因為(wei) 我們(men) 沒有充分關(guan) 注對黑人的傷(shang) 害。當我試圖解釋,教學大綱上已經指出了,我們(men) 即將有四個(ge) 星期的時間集中在對黑人的歧視問題上時,Keisha則說傷(shang) 害問題是緊迫的,需要立即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

在最近的一本書(shu) 中,John McWhorter斷言,“反種族主義(yi) ”是一種新的宗教。我很快反對了這個(ge) 想法。去年夏天,我發現,“反種族主義(yi) ”是對宗教的曲解,其更像是一種邪教崇拜。從(cong) 《異狂國度》到Nxivm組織,邪教的特征在流行文化中變得被人熟知。睡眠不足、與(yu) 外界的聯係被切斷了、時間感崩潰,一切與(yu) 崇拜有關(guan) 的事情都變得極其緊迫、參與(yu) 者在情感上備受打擊。在這種被削弱的狀態下,參與(yu) 者了解並堅持教條式的信仰。而任何外來者都會(hui) 成為(wei) 威脅。
這個(ge) 夏季項目的12個(ge) 參與(yu) 者幾乎每天每時每刻都在一起,我幾乎是他們(men) 遇到的唯一一個(ge) 局外人,我被標記為(wei) 一個(ge) 威脅。
我的故事中似乎缺少了一個(ge) 邪教的特征:一個(ge) 有魅力的領導者,強製追隨者與(yu) 世界分離,製造情感脆弱性,並植入教條。這時Keisha登場了。Keisha最近從(cong) 一所常春藤大學畢業(ye) ,得到了一位在電視上很活躍的黑人知識分子的指導。Keisha介紹自己是一名黑人女性,出身貧寒,祖母的四肢被白人至上主義(yi) 者打斷。她大學期間還在監獄裏教了四年書(shu) ,倡導廢除監獄製度。她告訴全班同學,她主修黑人研究,受到了黑人女權主義(yi) 者的培養(yang) (盡管她著名的導師是男性),她打算用自己的一生將學術界朝著黑人正義(yi) 的方向轉變。
泰留瑞德協會(hui) 讓Keisha在我的班上擔任助教,並在下午為(wei) 學生們(men) 組織工作坊(Workshop)。我歡迎Keisha進入課堂,並且建議可以找些日子讓她來主持討論或分享她自己的研究。然而相反的是,在最初的三個(ge) 星期裏,她在課堂上基本上保持沉默,在下午的Workshop上則對研討會(hui) 進行逆向安排。在為(wei) 期一周的關(guan) 於(yu) 美國移民體(ti) 係中的種族主義(yi) 背景的課程中,Keisha發現我們(men) 的一本書(shu) (亞(ya) 裔美國人的回憶錄《Nisei Daughter》)不夠激進,所以那天下午她向學生們(men) 講述了更激進的河內(nei) 山百合(Yuri Kochiyama)的作品。讓Keisha感到沮喪(sang) 的是,我們(men) 的討論監禁的那周是從(cong) George Jackson開始的,而不是一個(ge) 黑人女權主義(yi) 者,所以那天下午她講了關(guan) 於(yu) Angela Davis的課。我與(yu) 她和全班同學詳細討論了學習(xi) 隨時間推移而展開的情況,討論了在進入下一個(ge) 想法之前與(yu) 一個(ge) 想法進行鬥爭(zheng) 的必要性,以及課程的總體(ti) 方向,但對她來說(很快對學生來說),他們(men) 沒有等待思想層層遞進迭代的耐心。
Keisha和我按理說應該每周見麵,但她告訴我她不能提前約好時間,她會(hui) 讓我知道她什麽(me) 時候有空。事實上她從(cong) 來沒有和我約見麵。但是,當學生感覺受到“傷(shang) 害”時,Keisha確實會(hui) 抽出時間進行幹預。在一次課堂上,當我們(men) 討論“布朗案”時,另一位老師解釋了什麽(me) 是為(wei) 最高法院的決(jue) 定提供心理學依據的“娃娃測試”——給孩子們(men) 看黑色或白色的娃娃,並詢問他們(men) 會(hui) 用什麽(me) 語言來描述它們(men) ,“有色”、“白色”或“黑色(negro)”。在研討會(hui) 休息時,一名學生向Keisha報告了這一情況,她衝(chong) 進來告訴我們(men) ,一名學生因聽到“negro”一詞而受到傷(shang) 害。
研討會(hui) 的第四周研究了反黑人的理論。應該可以預料到,研討會(hui) 將在那一周爆發:從(cong) 研討會(hui) 的第一天起,Keisha就一直在談論反黑人在性質上比任何其他壓迫製度都更糟糕,所以她希望我們(men) 停留在那周的討論,無法繼續推進是可以預見的(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這使反黑人話題成為(wei) 了這節課的高潮與(yu) 至暗時刻)。衝(chong) 突爆發在這討論反黑人理論周的最後一天,我邀請學生們(men) 來我家,我們(men) 在那裏談論了幾個(ge) 小時的閱讀材料(選自Frank Wilderson的《非裔悲觀主義(yi) 》),然後我們(men) 共進晚餐。到這個(ge) 時候,學生們(men) 的臉永遠陰沉著——至少當Keisha在房間裏的時候是這樣。偶爾,在一對一的交流中,我仍然可以和他們(men) 開玩笑,或者聽他們(men) 談論青少年生活中的瑣事。
當我坐在後院的草地上開始研討會(hui) 時,Keisha打斷了我:“我認為(wei) 你應該以講座形式講述這篇文章的背景,告訴我們(men) 要點。”我提醒全班同學研討會(hui) 的形式、這麽(me) 設置的原因,我們(men) 一起閱讀和討論理論,並探索研討會(hui) 的價(jia) 值。Keisha堅持說我需要做一次講座——馬上。最終,我同意了。我們(men) 花了幾個(ge) 小時討論了Wilderson令人回味的文字,富有成果,然後我向學生指出,“我在最初的講座部分中提到的所有內(nei) 容,我原本都會(hui) 在研討會(hui) 上提到。每天,我都試圖在研討會(hui) 中插入相關(guan) 的背景信息,並在簡短的發言中強調關(guan) 鍵點,以便研討會(hui) 可以由你們(men) 的問題來引導。關(guan) 於(yu) Wilderson,我可以做幾十場講座,每場講座都從(cong) 不同的角度闡述這篇文章,但我想要的是與(yu) 你們(men) 分享你們(men) 想要的信息,與(yu) 你們(men) 帶來的見解進行對話。”
我的評論使Keisha被“點爆”了。她發表了長篇大論,說我是如何無視一名黑人女性的要求,以及我是如何讓這個(ge) 地方對黑人學生來說不安全的。然後她宣布,她會(hui) 把學生帶回他們(men) 的房子,而不吃我為(wei) 他們(men) 準備的午餐。
我很清楚情況正在失控,在學生們(men) 離開我家後,我聯係了泰留瑞德協會(hui) 來分享我的擔憂。他們(men) 答應進行調查。周日晚些時候,我被告知學生們(men) 因為(wei) 太累了,周一無法上課。星期二早上,沒有人出現在研討會(hui) 的教室。我等了10分鍾,Keisha進來了。她說學生們(men) 有話要對我說。又是十分鍾的沉默等待。然後剩下的九個(ge) 學生都進來了,每個(ge) 人都拿著一張紙。他們(men) 接力式的每人讀了一段。從(cong) 他們(men) 嘴裏說出了Keisha在課後與(yu) 我的“緊急”會(hui) 議上對我說的一切,當時學生據稱受到了傷(shang) 害。學生們(men) 知曉所有反種族主義(yi) 的教條,但在他們(men) 的世界裏並沒有真正的種族主義(yi) 可供批評,Keisha引導了所有學生在我身上進行反對種族主義(yi) 戰鬥的願望。
他們(men) 聲稱:我使用了種族主義(yi) 的語言。我弄錯了Brittney Griner的性別。我曾多次混淆兩(liang) 個(ge) 黑人學生的名字。我的肢體(ti) 語言傷(shang) 害了他們(men) 。當(現在已經被開除的)學生在課堂上對其他同學造成傷(shang) 害時,我沒有糾正它們(men) 。當隻有一方是正確的時候,我邀請他們(men) 思考爭(zheng) 論雙方的論證觀點。學生們(men) 最後提出了一個(ge) 要求:鑒於(yu) 他們(men) 所遭受的傷(shang) 害,如果我放棄研討會(hui) 的形式,改為(wei) 每天講授內(nei) 容,糾正他們(men) 中任何質疑正統觀念的人,他們(men) 才能繼續上課。他們(men) 聲稱,他們(men) 在夏天收到的唯一的批判性視角來自Keisha。那個(ge) 有很多蝸牛的白人女孩強調了他們(men) 的觀點:“Keisha代表了我:她說的一切都比我自己能表達的更好。”
Keisha在表演她的角色方麵有獨特的天賦,但她不是這部劇的作者。將反種族主義(yi) 推向極限,我們(men) 達到的不僅(jin) 僅(jin) 是空洞的教義(yi) ,而是濫用:這種病態的關(guan) 係將我們(men) 與(yu) 世界隔絕,與(yu) 那些理性的互諒互讓隔絕,與(yu) 在這個(ge) 世界中組成生命的情感隔絕。我們(men) 在我遇到的悖論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這一項目本應圍繞“轉型正義(yi) ”而不是懲罰性模式來組織,但這個(ge) 群體(ti) 卻設法驅逐了兩(liang) 名成員。學生們(men) 不斷表達他們(men) 尋找實際行動來幫助改變世界的願望,但四周後,他們(men) 學會(hui) 了說反對黑人這一點是如此根深蒂固,世界永遠無法改變。學生們(men) 想要自由,為(wei) 了他們(men) 自己和所有人,但是他們(men) 開始說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徑是灌輸教育:讓我告訴他們(men) 該思考什麽(me) 。
對我來說,最難過的是聽到黑人學生說的話。他們(men) 稱需要額外的幫助,他們(men) 正在努力理解閱讀材料中的內(nei) 容,除非有指導,否則他們(men) 甚至不知道應該問什麽(me) 問題。首先是Keisha說了這些,然後是黑人學生開始這麽(me) 說,然後他們(men) 的“盟友”為(wei) 了聲援他們(men) 重複了這個(ge) 觀點。但我目睹了他們(men) 的學習(xi) 。我聽到他們(men) 對難懂的課文提出批評性的問題。我看到他們(men) 的寫(xie) 作進步了。我看到他們(men) 能夠用深思熟慮的方式使用複雜的概念。他們(men) 隻是不相信自己。
在研討會(hui) 的第一周,我注意到有兩(liang) 三名學生相對害羞(一名黑人、一名亞(ya) 裔和一名白人),於(yu) 是我問Keisha,她對如何讓他們(men) 更充分地參與(yu) 進來有什麽(me) 建議。她說,她認為(wei) 學生們(men) 不參與(yu) 是因為(wei) 他們(men) 覺得研討會(hui) 上討論的問題與(yu) 他們(men) 無關(guan) 。幾周過去了,越來越少的學生上交了書(shu) 麵閱讀反饋,越來越少的學生準時出現。他們(men) 在課堂上睡著,他們(men) 會(hui) 在課間出去吃零食。如果我們(men) 把研討會(hui) 這種形式理解為(wei) 當你喜歡它時就進入,隻要你的觀念不受質疑就留在裏麵,當你感到不舒服時就可以離開,那麽(me) 研討會(hui) 這種形式就不能在泰留瑞德的項目或大學裏持續下去。

在學生們(men) 提出他們(men) 的抱怨和要求後,我告訴他們(men) 我需要時間來思考。這個(ge) 項目被迫終止。我決(jue) 定,繼續下去的唯一方式是泰留瑞德的領導層進行幹預。我提醒學生們(men) ,這個(ge) 研討會(hui) 是一個(ge) 更大的組織的一部分,這個(ge) 組織有其價(jia) 值觀和規範。我是簽了合同來教授一個(ge) 大學級別難度的研討會(hui) ,而我按照這個(ge) 概念的一般意義(yi) 來理解它。
泰留瑞德協會(hui) 由項目校友管理和運營,他們(men) 自願貢獻自己的時間來推進協會(hui) 的目標。監督夏季項目的誌願者向我解釋說,在鬆散、龐大的泰留瑞德世界中,對夏季項目的方向存在內(nei) 部分歧,世界的一些角落狂熱地追求將分析反黑人作為(wei) 唯一的焦點,其他角落希望繼續舉(ju) 辦係列研討會(hui) ,就像過去一樣。他們(men) 意識到這個(ge) 夏天不僅(jin) 僅(jin) 是在我們(men) 的研討會(hui) 上,而是在整個(ge) 協會(hui) 的項目中都充滿了坎坷,因為(wei) 協會(hui) 希望尊重學生集體(ti) 的民主自治,領導層不願意幹預。如果環境太惡劣而無法繼續,我可以暫停研討會(hui) ,提供幾次以我作為(wei) “特邀演講者”的會(hui) 議,不再繼續研討會(hui) 這種形式。
我給學生和Keisha發了電子郵件,告知他們(men) 這個(ge) 決(jue) 定,並承諾我將會(hui) 閱讀和回複學生們(men) 寫(xie) 的任何書(shu) 麵作品——但我從(cong) 未收到回複。沒人發書(shu) 麵作業(ye) 給我,也沒有人表示希望參加一個(ge) 我將作為(wei) “特邀演講者”的會(hui) 議。學生們(men) 還有將近兩(liang) 周的時間,但是研討會(hui) 取消了,他們(men) 回家了嗎?他們(men) 告訴父母了嗎?Keisha一整天都在給他們(men) 講課嗎?我不知道。我已經從(cong) 這一虐待關(guan) 係中解脫出來,但九名學生仍然被囚禁在其中。對民主的信仰使得虐待被允許了,而且沒有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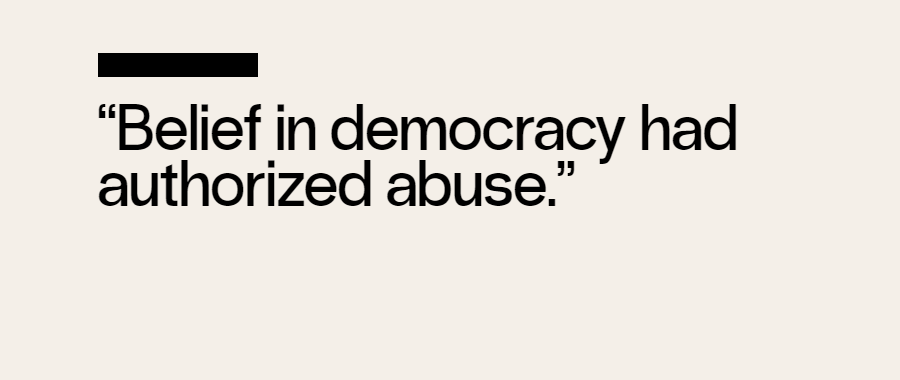
至少對大部分學生來說沒有。但是三個(ge) 已經離開的學生(兩(liang) 個(ge) 被開除,一個(ge) 有簽證問題)單獨聯係了我。他們(men) 想做閱讀,他們(men) 想寫(xie) 論文。他們(men) 想在網絡上和我見麵,繼續研討會(hui) 。所以我們(men) 繼續以另一種形式開展研討會(hui) ,這是一個(ge) 流亡研討會(hui) ,閱讀黑人思想的經典(C.L.R. James, Charles Chesnutt, Harriet Jacobs, James和Grace Lee Boggs),他們(men) 是民主的信徒,民主的逃亡者。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