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ge) 多世紀來,美國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一直處於(yu) “改變但不結束”的狀態。1987年16%的白人男性認為(wei) 平權運動“過頭了”,1994年57%的白人男性反對平權運動,2019年約73%的美國人反對平權運動的不公正待遇。2020年“弗洛伊德案”引發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在美國持續發酵,許多參與(yu) 者都曾是平權運動的受益者。
在他們(men) 眼中,美國社會(hui) 並沒有因平權變得更平等、更公正,美國的政治認同反而麵臨(lin) 空前危機。為(wei) 什麽(me) 美國越平權,政治認同越分裂?目前,國內(nei) 對美國平權運動的研究以探討運動發展脈絡或平權個(ge) 案的論著居多,研究平權運動與(yu) 美國政治認同關(guan) 係的作品則不多見。
鑒於(yu) 此,本文嚐試從(cong) 平權運動曆史演變的視角出發,重新反思平權運動自身的目標與(yu) 初衷,考察平權運動對美國政治認同的影響。
一 平權運動的本質、理由以及發展曆程
平權運動是美國政府主要為(wei) 改善少數族群和婦女的社會(hui) 經濟狀況,消除就業(ye) 、教育等領域的種族與(yu) 性別歧視而製定和施行的一係列補償(chang) 性計劃。
它起源於(yu) 羅斯福和杜魯門時期的公平就業(ye) 、廢除軍(jun) 隊種族隔離等行政命令,以1965年林登·約翰遜總統簽署的第11246號行政命令為(wei) 重要標誌,正式登上曆史舞台。無論支持、反對或者調整,美國曆屆政府都要在這一問題上表明立場。平權運動不僅(jin) 涉及美國社會(hui) 最敏感的種族及民權問題,也牽涉到憲法解釋、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社會(hui) 文化與(yu) 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麵。平權運動的本質是通過尋求公正與(yu) 機會(hui) 平等,鞏固美國信念,凝聚美國精神,增進美國人的政治認同。
一般認為(wei) ,美國推動平權運動基於(yu) 以下四點理由:
1.反對社會(hui) 歧視。依據1877年《憲法修正案》第14條和1964年《民權法案》第7條,國家采取各類積極措施以矯正曆史或現實中的歧視,如高校錄取少數族裔學生政策、就業(ye) 指標與(yu) 配額、承包合同預留製等。1986年“鋼鐵工人訴就業(ye) 機會(hui) 平等委員會(hui) 案”(Sheet Metal Workersv.EEOC,478U.S.421)即以反歧視理論確立了平權運動的合法性。
2.補償(chang) 弱勢群體(ti) 。鑒於(yu) 黑人長期受到奴隸製與(yu) 種族隔離製的影響,婦女也深受性別歧視的影響,支持者認為(wei) 過去的歧視與(yu) 現在的弱勢狀態存在必然聯係,應當在各類社會(hui) 政策上給予該類人群以優(you) 惠待遇。這一補償(chang) 性公正理論,不僅(jin) 要求對過去的不平等進行補償(chang) ,而且要對因過去不平等造成的今日困境進行補償(chang) 。
3.建立示範效應。在政策的支持下,少數族裔與(yu) 女性在社會(hui) 各領域脫穎而出將有助於(yu) 打破傳(chuan) 統思維定勢,為(wei) 處於(yu) 社會(hui) 不利地位的人群樹立榜樣,增強“美國夢”的現實吸引力,增進社會(hui) 穩定。
4.尋求社會(hui) 多元化。多元化理論認為(wei) ,無論少數族裔或白人,男性、女性或跨性別人群,動態平衡的多元社會(hui) 將使每一位公民受益,社會(hui) 寬容將有利於(yu) 社會(hui) 共識與(yu) 政治認同的形成。
平權運動發展至今已有半個(ge) 多世紀,但對於(yu) 該運動的曆史定位卻始終處於(yu) 變動之中。
以加利福尼亞(ya) 州人事局民權處的定義(yi) 為(wei) 例,平權運動由先前的旨在“采取措施以獲得平等雇用機會(hui) 並糾正過去或現在的雇用歧視所造成的影響”的係列政策,轉變為(wei) “采取主動和非優(you) 先的措施以獲得平等雇用機會(hui) 和非歧視雇用行為(wei) ”的運動。
前後幾近矛盾的表述方式,說明平權運動的內(nei) 涵在變遷過程中發生了明顯變化。為(wei) 了便於(yu) 研究,學界一般將其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
1.維權時期: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該時期政策旨在維護少數族裔與(yu) 婦女的權益,提升他們(men) 在經濟與(yu) 政治上的獲得感、歸屬感。
鑒於(yu) 戰時經濟需求與(yu) 軍(jun) 隊人員短缺的現實,1941年羅斯福建立了臨(lin) 時公平就業(ye) 實踐委員會(hui)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ttee,FEPC),嚐試以行政命令(第8802號)的方式改變職場的種族與(yu) 性別偏見。到戰爭(zheng) 結束時,共有超過一百萬(wan) 黑人入伍,近三百萬(wan) 婦女投身軍(jun) 工產(chan) 業(ye) 與(yu) 後勤保障等工作。
這一行政命令為(wei) 1964年《民權法案》第7條反歧視條款奠定了基礎,被黑人譽為(wei) 第二份《奴隸解放宣言》。作為(wei) 第一個(ge) 加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hui) 的總統,杜魯門充分認識到種族歧視對戰後經濟發展及冷戰政策的不利影響,1948年7月他連續頒布兩(liang) 大行政命令,要求在聯邦政府和軍(jun) 隊中徹底廢除種族隔離。
1963年6月,肯尼迪總統在行政命令(第11114號)中正式提出推進平權運動的要求——“消除在涉及聯邦財政資助之事業(ye) 的雇用問題上,由於(yu) 種族、宗教信仰、膚色或族裔背景而發生的歧視性行為(wei) ”。這些總統行政命令最終以1964年《民權法案》的方式確立下來。1965年9月,約翰遜總統的第11246號行政命令取代了肯尼迪時期的第10925號與(yu) 第11114號政令,為(wei) 平權行動在更廣泛意義(yi) 上的應用和詮釋奠定了法律基礎。
2.優(you) 待時期: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該時期政策旨在優(you) 待少數族裔,也稱為(wei) 平權運動的全盛期。
尼克鬆總統時期,平權運動已經不滿足於(yu) 有限的維權,轉而更多地開始尋求優(you) 待少數族裔,以目標和時間表(goals and timetables)的方式對少數族裔在教育、就業(ye) 中的占比作出嚴(yan) 格而詳細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隨著聯邦最高法院的介入,平權運動的合憲性問題得到了社會(hui) 的廣泛關(guan) 注。
美國社會(hui) 開始反思:以硬性配額製為(wei) 標配的平權運動是否能夠有效糾正社會(hui) 歧視?在招生與(yu) 雇用過程中,如何以精確裁剪(precisely tailored)的方式,既體(ti) 現平等保護條款的普遍適用原則,也體(ti) 現美國社會(hui) 多元化特征?總體(ti) 而言,平權運動全盛期的政策更著眼於(yu) 提升少數族裔的社會(hui) 存在感,以群體(ti) 補償(chang) 的方式強行推動少數族群融入主流社會(hui)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反向歧視與(yu) 象征性種族主義(yi) 的後果。
3.平等時期: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該時期政策旨在尋求多數族裔成員與(yu) 少數族裔成員的權益平等。
關(guan) 於(yu) 這一時期的平權運動,有兩(liang) 種不同的評價(jia) 。一種看法認為(wei) ,平權運動受到限製並逐漸消亡。裏根與(yu) 布什政府以平等為(wei) 己任,向現實中已扭曲為(wei) 配額製的平權運動發起攻擊。優(you) 待與(yu) 配額逐步為(wei) 個(ge) 人考績與(yu) 開放競爭(zheng) 所取代。進入90年代後,平權運動淹沒在種族多元化的話語中。多個(ge) 州成功地以動議形式修改州憲法或州法律,反對任何優(you) 待性政策,如1996年加利福尼亞(ya) 州的“209提案”(Proposition 209),1998年華盛頓州的“200動議”(Initiative 200),2006年密歇根州的“第二計劃”(Proposal 2),2008年內(nei) 布拉斯加州的“424動議”(Initiative 424)等。新的州憲法或/和法律規定,“本州在處理公共就業(ye) 、公共教育或公共訂約合同上,不得基於(yu) 種族、性別、膚色、族群性或族裔背景而歧視或優(you) 待任何個(ge) 人或群體(ti) ”。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wei) ,平權運動在平等時期走向成熟。1978年後,政府開始反思一刀切式的種族優(you) 待措施,以避免出現建立在種族基礎上的新歧視。而2003年的兩(liang) 項密歇根大學入學案[“格魯特訴伯林格案”(Grutter v.Bollinger)與(yu) “格拉斯訴伯林格案”(Gratz v.Bollinger)]判決(jue) 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wei) ,多元化是政府需保障的急迫利益,平權措施依然是鞏固差異性社會(hui) 的有效手段。
同樣,2020年“公平入學組織訴哈佛大學案”[Studentsfor Fair Admission(SFFA)v.Harvard]中,美國聯邦法院的裁決(jue) 認為(wei) ,哈佛大學在招生過程中並沒有歧視亞(ya) 裔學生,考量種族因素是為(wei) 了保證大學的多元化,符合憲法規定。雖然研究者已經指出,以功利性的多元化政策來重塑、補充或取代基於(yu) 權利的平權行動政策可能會(hui) 引發新矛盾,但人們(men) 依然看到,越來越多的入學及就業(ye) 歧視已經完美繞開“功能性配額製”“機械性優(you) 待”或憲法第14條修正案保護的平等權問題。在多元化名義(yi) 下,以非優(you) 先的措施獲得平等機會(hui) ,成為(wei) 平權運動的新定義(yi) 。
二 平權運動對政治認同的影響
在維權-優(you) 待-平等的曲折進程中,平權運動不斷調整政策方向,以實現社會(hui) 公正與(yu) 機會(hui) 平等。
一方麵,該運動部分實現了矯正社會(hui) 歧視、補償(chang) 弱勢群體(ti) 、實現多元化社會(hui) 的目標;另一方麵,平權運動也對美國民眾(zhong) 的政治認同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
首先,平權政策導致國家權力擴張,國家整體(ti) 性認同斷崖式下滑。
在美國州權主義(yi) 傳(chuan) 統中,保障公民權利是州及地方政府的內(nei) 務,但平權運動以來,聯邦法院卻陸續推翻各地區歧視性法案,重釋憲法第14修正案中“平等”的內(nei) 涵。1952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hui) 案”(Brown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宣告了“隔離但平等”原則在教育領域的終結。
麵對南方地區的大規模抵製,聯邦政府和國會(hui) 堅定地站在最高法院一邊:1957年9月,艾森豪威爾總統派遣聯邦軍(jun) 隊進駐阿肯色州小石城,護衛9名黑人中學生進校學習(xi) ;1962年10月,肯尼迪總統收編密西西比州民兵為(wei) 聯邦軍(jun) 預備隊,維持密西西比大學校園及城市治安,保障該校招收的首位黑人學生正常學習(xi) ;國會(hui) 也在短時間內(nei) 頒布了1964年《民權法案》、1965年《選舉(ju) 權法案》等多個(ge) 保障平權運動成果的法案。
聯邦政府借助於(yu) 平權政策,不僅(jin) 將權力觸手成功地伸向教育、就業(ye) 等傳(chuan) 統上隸屬於(yu) 州權的領域,而且力量持續增強。為(wei) 增加少數族裔就業(ye) 、改變傳(chuan) 統雇用慣例,1969年尼克鬆政府建立“費城計劃”,要求聯邦合同的承包商在雇用過程中必須製定增加少數族裔就業(ye) 的目標與(yu) 時間表。
該政策被視為(wei) 此前配額製的替代品,受到各州抵製。除費城、聖路易斯、亞(ya) 特蘭(lan) 大等少數城市外,大部分地區依然自行確定雇用目標。平權運動的抵製浪潮加劇了美國國家認同的分裂。20世紀50年代末,超過85%的民眾(zhong) 為(wei) 美國政府與(yu) 政治製度感到自豪。進入平權運動全盛期後,民眾(zhong) 投票率與(yu) 國家認同感急劇下降。
裏根與(yu) 老布什總統勾勒的平權簡易公式(平權=定額=不公正)拉低了公眾(zhong) 對平權運動支持度,國家認同出現了短暫的整體(ti) 性回暖。從(cong) 90年代開始,披著多元化外衣的平權運動繼續撕裂美國社會(hui) 。總統奧巴馬推動婚姻平權的做法並沒有挽回頹勢,反而推動了選民政黨(dang) 選擇(party sorting)的進程,加劇了政治種族化與(yu) 極化,國家認同迅速衰落。特朗普於(yu) 2018年宣布廢除奧巴馬的各項平權政策後,引發各州抵製。
2020年加州立法機關(guan) 推出“ACA 5提案”取代1996年的“209提案”,允許加州在雇用問題及加州大學係統內(nei) 采取更加積極的平權政策,以此來對抗特朗普的種族主義(yi) 立場,美國國家認同降至穀底。
其次,平權運動的示範效應引發“權利泛化”,政治認同陷入“部落化”僵局。
平權運動激起的“權利革命”釋放了各類群體(ti) 尋求“賦權與(yu) 解放”的強大動能。權利朝向兩(liang) 個(ge) 維度迅速泛化:權利主體(ti) 的擴散和權利內(nei) 容的擴展。一方麵,白人男性享有的權利向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跨性別人群、移民、兒(er) 童甚至動物擴散;另一方麵,政治自由權利也逐步向社會(hui) 和經濟權利、福利主義(yi) 、環境權利、文化權利等方向深化。在“黑人權”的激發下,70年代開始的“褐色權”(拉美裔)、“紅色權”(印第安人)、“同誌權”運動極大地改變了平權運動的內(nei) 涵和樣貌。
1969年尼克鬆總統第11478號行政命令將婦女納入不得歧視的清單,1998年克林頓總統第13087號行政命令將性取向納入不得歧視的清單,2014年奧巴馬總統第13672號行政命令將性別認同納入不得歧視的清單。
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逐步取消奧巴馬政府的各項保護跨性別者(允許跨性別者服役、享受醫療保健、使用自己認同的廁所)及婦女墮胎權、避孕權政策。2021年拜登執政首日,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恢複上述權利。
傳(chuan) 統的政治認同多從(cong) 整體(ti) 理念或意識形態角度出發,認同對象包括國家、政治製度、階級、政黨(dang) 、政策等。而今的認同對象在差異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顯出“小而多”的“部落化”特征:人們(men) 不再討論國家認同,隻關(guan) 心少數族裔認同、移民認同、女性認同、性少數群體(ti) (LGBT)認同等。身份認同成為(wei) 美國當前的時代症候。
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表明,對同性戀的廣泛承認已超越黨(dang) 派分歧。繼2015年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後,民主黨(dang) 與(yu) 共和黨(dang) 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於(yu) 2017年達至曆史新高,分別為(wei) 83%與(yu) 54%。2019年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在75%與(yu) 44%。
跨性別群體(ti) 的接受度則顯示出鮮明的黨(dang) 派分歧。2016年數據顯示,67%的民主黨(dang) 人支持為(wei) 變性人提供正常的婚禮服務,而超過71%的共和黨(dang) 人反對這一服務。隨著社會(hui) 對邊緣群體(ti) 接受度的迅速提升,他們(men) 已經不滿足於(yu) 在法律、製度上受到與(yu) 主流群體(ti) 相同的待遇,轉而要求社會(hui) 廣泛認可甚至讚頌他們(men) 的獨特性與(yu) 差異性。
亞(ya) 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道明了這一認同的心理基礎:他們(men) 可能並非因為(wei) 匱乏,而是更希望被關(guan) 注、被讚許,他們(men) 真正感興(xing) 趣的是受到他者的承認。邊緣群體(ti) 的認同不但無法凝聚政治共識,反而加速了“從(cong) 單一認同到諸多認同”的政治認同分裂過程。
再次,平權政策拉低了社會(hui) 的智識標準,政治共識難以凝聚。
蘇珊·雅各比在《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一書(shu) 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反理性主義(yi) 與(yu) 無知的流行文化(萬(wan) 物的視頻化、圖像化,以迎合教育低水平人群需求)互相促進下,美國特有的反智主義(yi) 傾(qing) 向大大加劇。向邊緣群體(ti) 的政策傾(qing) 斜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社會(hui) 的智識標準。
從(cong) 80年代開始,軍(jun) 隊與(yu) 媒體(ti) 以“部隊”(troop)替代原有的暗含男性特質的“士兵”(soldier),以顯示對女性的尊重,卻毫不顧及作為(wei) 集體(ti) 名詞的“部隊”一詞應有的使用方式。其結果是,凡有美國人卷入的軍(jun) 事衝(chong) 突,記者均統一報道為(wei) “X個(ge) 部隊陣亡”。關(guan) 於(yu) 婦女墮胎問題的政策辯論中也充斥著反智主義(yi) 的聲音。
2007年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安東(dong) 尼·肯尼迪撰寫(xie) 的支持禁止“部分生產(chan) 墮胎術”(一種妊娠中後期流產(chan) 術)的判決(jue) 意見中,作為(wei) 判決(jue) 依據的“墮胎綜合征”並沒有任何可靠研究支撐,僅(jin) 以反墮胎組織收集的傳(chuan) 聞作為(wei) 審判依據。此外,美國總統小布什和特朗普逢迎公眾(zhong) 的言行,也進一步將國家推入反智主義(yi) 的深淵。
前者用“常出錯但也常自嘲”的天真形象吸引南部大媽的選票;後者全天候使用推特(Twitter)這一限於(yu) 140字符的社交媒體(ti) 發表政見,以斷章取義(yi) 的方式吸引非理性人群,還在競選中向反對平權運動的“紅脖子”支持者宣告“我熱愛教育程度低的人”,依靠不斷嘲諷知識分子與(yu) 專(zhuan) 家來贏得大眾(zhong) 的支持。
反智主義(yi) 的政治化使得國家領導者失去了凝聚國家共識的基本能力。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2001年“9·11事件”後的兩(liang) 個(ge) 月,74%的美國人認為(wei) 國家是團結的,到了2004年小布什競選連任時,該比例跌落至45%。
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以黨(dang) 派政治的方式撕裂社會(hui) ,超過77%的美國人認為(wei) 國家已陷入分裂,出現了現實版的“兩(liang) 個(ge) 美國”(Two Americas),而特朗普本人也被視為(wei) “分裂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最後,平權運動的溢出效應加劇政治認同兩(liang) 極化趨勢。
平權運動深刻改變了少數族裔、性少數群體(ti) 、婦女、學生的社會(hui) 處境,其政策也在美國兩(liang) 黨(dang) 的力量對比、意識形態變遷、政治結構重塑等方麵產(chan) 生溢出效應,推動了政治認同極化的進一步加劇。
一方麵,平權運動引發的核心選民變動加大了兩(liang) 黨(dang) 政治的極化。阿維迪特·阿查裏亞(ya) 認為(wei) ,美國南方地區的白人從(cong) 平權運動初期即開始陸續脫離民主黨(dang) ,這一過程隨著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ju) 權法案》通過而加快。當1980年羅納德·裏根當選總統時,南方白人就已經穩定地成為(wei) 共和黨(dang) 人的票倉(cang) 。經濟全球化持續拉大美國貧富差距,作為(wei) “故土陌生人”的南方白人排外主義(yi) 情緒迅速高漲,最終導致特朗普當選及政治極化的加劇。
進入新世紀後,兩(liang) 黨(dang) 在推進平權運動問題上的分歧增大。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民主黨(dang) 及其支持者“認為(wei) 國家需要進一步推進平權”的比例從(cong) 2010年的57%上升到2017年的81%,而共和黨(dang) 及其支持者讚同平權的比例則一直徘徊在32%左右。兩(liang) 黨(dang) 政治極化成為(wei) 當前美國政治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麵,平權運動引發的“權利革命”成為(wei) 政治文化兩(liang) 極化的根本動力。人們(men) 對同性戀、跨性別與(yu) 移民問題的接受度呈現“此起彼落”的差異態勢:民主黨(dang) 大踏步向進步主義(yi) 方向邁進,而共和黨(dang) 在平權問題上止步不前。
有學者認為(wei) ,這一文化的撕裂與(yu) 衝(chong) 突主要由民主派“自由化加速”所導致,共和黨(dang) 人的憤怒隻是“被圍困心態”的一種表現。但也有相反的觀點認為(wei) ,平權運動導致的政治認同兩(liang) 極化可能隻是一種“幻影”(phantom)而已。美國政治認同極化呈現出的複雜樣貌,由此可見一斑。
三 平權運動中的政治認同困境及其原因
平權運動的初衷是通過一係列政策措施調整,允許將種族、原籍、性別、殘疾等作為(wei) 重要衡量因素,給曆史上或現實中遭到歧視或將來可能重新遭受歧視的群體(ti) 提供機會(hui) ,以實現社會(hui) 公正與(yu) 機會(hui) 平等,增進公民的政治認同。
但在施行過程中,平權運動卻麵臨(lin) 著“越平權越分裂”的困境:越是積極推進平權運動,該運動就越脫離整體(ti) 性政治認同的目標,轉向差異化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認同。這一旨在強調少數群體(ti) 利益的亞(ya) 群體(ti) 認同強化了人們(men) 對社會(hui) 不公正的感受,分裂並稀釋了現有的政治認同。受害者心態是平權運動中政治認同困境的主要表現形式。
首先是語義(yi) 歧視問題。通過將Nigger/Negro(黑人)改造為(wei) 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國人),Manpower(男勞動力)改造為(wei) Workforce(勞動力),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le) )改造為(wei) Happy Holiday(節日快樂(le) ),平權運動完成了美國文化中族裔、性別、宗教等特定語義(yi) 的轉換,強化了亞(ya) 群體(ti) 作為(wei) 受害者的集體(ti) 認同。其次是反向歧視問題。
從(cong) 20世紀90年代起,憤怒的白人男子站到了反對平權運動的最前列:在外,婦女和少數族裔奪走了他們(men) 的經濟與(yu) 政治力量;在內(nei) ,妻子奪走了他們(men) 的家庭權威。2016年總統大選,正是這群自認為(wei) “平權運動最大的受害者”將特朗普送上了總統寶座。此外,有關(guan) 亞(ya) 裔是平權運動受益群體(ti) 抑或是受害群體(ti) 的爭(zheng) 論也顯示出反向歧視的另一側(ce) 麵。
2018年亞(ya) 裔人口占比為(wei) 6.7%,卻占到哈佛大學新生錄取比例的22.9%。很多人指責平權運動的真正贏家是亞(ya) 裔,但亞(ya) 裔卻自認為(wei) 是這場運動不折不扣的受害者。1970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5歲以上的美國男性中,大學以上學曆的中國裔在本族群樣本占比約30.8%,英國二代移民占比約17.5%。1990年人口普查時,碩士及以上學曆的中國大陸一代移民占比為(wei) 約25.3%,與(yu) 威爾士一代移民並列第一。
聯邦政府雖未正式下文,但90年代以後已逐步將亞(ya) 裔排除在平權運動之外。在亞(ya) 裔看來,平權運動削減並限製了自己的錄取名額,如果廢除平權運動,他們(men) 將憑借自己的成績優(you) 勢占據五分之四的非裔、拉丁裔錄取名額,將錄取率從(cong) 目前的18%提升至23%,無需再出現“亞(ya) 裔偽(wei) 裝黑人被頂級醫學院錄取”這樣的鬧劇。最後是汙名化問題。
1982年羅格斯大學卡姆登學院(Rutgers University Camden College)的心理學研究者證實,當人們(men) 意識到平權運動影響大學錄取政策時,即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被錄取的少數族裔的學術能力與(yu) 白人學生相差甚遠,除非他們(men) 表現出超凡的競爭(zheng) 力,否則將被整體(ti) 性汙名化。
無論語義(yi) 歧視、反向歧視或汙名化,都表明平權運動對不同人群造成的實際心理創傷(shang) 。平權運動在推進過程中沒有增進人們(men) 對於(yu) 公正、正義(yi) 的真切感受,反而強化了受害者群體(ti) 的認同。
從(cong) 社會(hui) 心理的角度而言,形成上述政治認同困境的原因有以下兩(liang) 點。
第一,人們(men) 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降低。
托克維爾認為(wei) ,真正困擾美國人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平等的感覺,當社會(hui) 地位極度不平等時,不平等本身是不刺眼的,但是當人人劃一時,微弱的差異也能引起巨大反感。亨廷頓也觀察到了類似的現象。他認為(wei) 廢奴主義(yi) 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以及耙糞運動出現在進步主義(yi) 時代的原因,並非奴隸製在19世紀30年代變得更加邪惡,也並非進步主義(yi) 時代腐敗陡然增多,而是在那個(ge) 曆史時期公眾(zhong) 對於(yu) 這類現象的容忍程度降低了。
到了21世紀,黑人認為(wei) 社會(hui) 對自己補償(chang) 不夠、歧視增多,同樣也是基於(yu) 該群體(ti) 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降低的原因。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對平權運動的原則性支持或反對直接取決(jue) 於(yu) 人們(men) 對於(yu) 歧視問題的迫切性及嚴(yan) 重程度的感知。
16%的白人認為(wei) 社會(hui) 存在大量歧視,而持這一觀點的黑人約有57%;28%的白人認為(wei) 政府更照顧黑人,有57%的黑人認為(wei) 政府更照顧白人,幾乎沒有黑人認為(wei) 政府在政策上偏向自己。相形之下,黑人具有更強烈的不平衡感,更低的獲得感,對於(yu) 社會(hui) 不公的感知也更為(wei) 敏感。
第二,人們(men) 對自我感覺的重視程度提高。
20世紀90年代以來,平權運動中出現的各種無理取鬧的訴訟充斥著媒體(ti) ,例如,體(ti) 重640磅的男子起訴巴爾的摩,稱該市違反憲法,拒絕承認他的肥胖是一種殘疾,這影響了他在市政合同競標上的優(you) 先權;某大學的男學生組織以性別歧視提起訴訟,狀告當地酒吧把“女士之夜”的第一杯啤酒免費送給女大學生,而不是男生;非裔雇員提起訴訟,稱深膚色的黑人老板開除她的原因是她膚色太淺。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訴訟理由背後,是“永遠相信你的感覺”這類廣告語所反映的社會(hui) 共識。
2001年“9·11”事件後的美國社會(hui) 長期浸淫在恐懼與(yu) 焦慮之中,“感覺不對勁”的對象也早已從(cong) 地鐵站某個(ge) 可疑的行李箱轉移到了大學課堂、企業(ye) 招聘等類似場景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危險無處不在,歧視無處不在。“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成為(wei) 各類亞(ya) 群體(ti) 社會(hui) 交往時最常佩戴的有色眼鏡。
信奉消費者(學生)至上的大學校園,也開始識時務地轉變了教育原則——大學教育,不在於(yu) 讓學生思考,而是要讓他們(men) 感到舒適。感覺舒適替代自由、平等成為(wei) 美國青年一代的新信條。他們(men) 的訴求不再是得到平等對待,而是讓自己感到舒適的特殊對待。自我感覺至上猶如一把利刃,割裂了美國社會(hui) ,無論是身份政治認同還是國家認同,都陷入了無盡的分裂之中。
本文撰寫(xie) 期間,大批受益於(yu) 平權運動的少數族裔、女權主義(yi) 者、性少數群體(ti) 走上街頭支持“黑命貴”抗議活動。2020年9月3日,在沒有警察警告或挑釁情況下,洛杉磯持槍歹徒當街射殺警員;9月22日,紐約、波特蘭(lan) 、西雅圖三大城市,被正式列為(wei) “無政府主義(yi) 管轄區”。與(yu) 參與(yu) 者不斷上升的政治熱情相伴的,是美國政治認同的進一步分裂。“美國人唯一的共識是大家沒有共識。”
無論是左派精英強調的多元文化為(wei) 目的的政治認同觀,還是右派帶有種族化傾(qing) 向的政治認同觀,都已經不足以彌合美國社會(hui) 現有的裂痕。
或許,正如查爾斯·泰勒所說的那樣,同一性與(yu) 統一性並非美國共和傳(chuan) 統的重心所在,尋求一種非民族主義(yi) 的、注重公民文化與(yu) 實踐、強調參與(yu) 的政治認同,才是美國政治未來的重塑方向。作者周順,係上海政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講師注釋從(cong) 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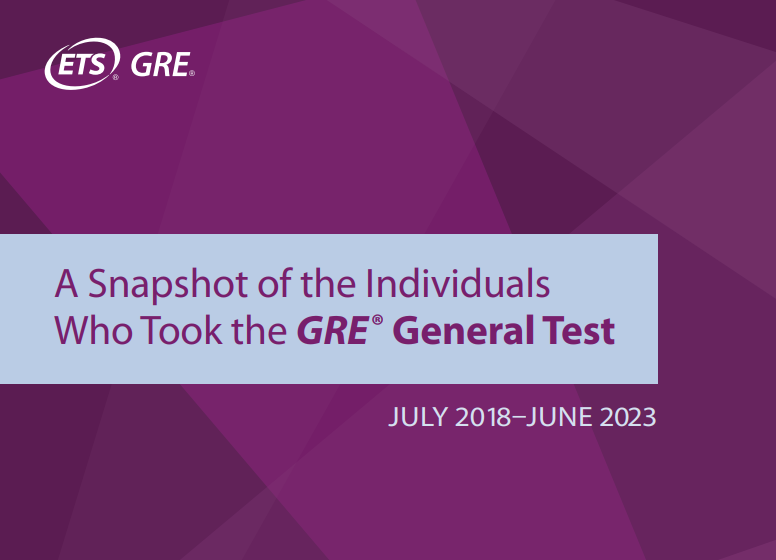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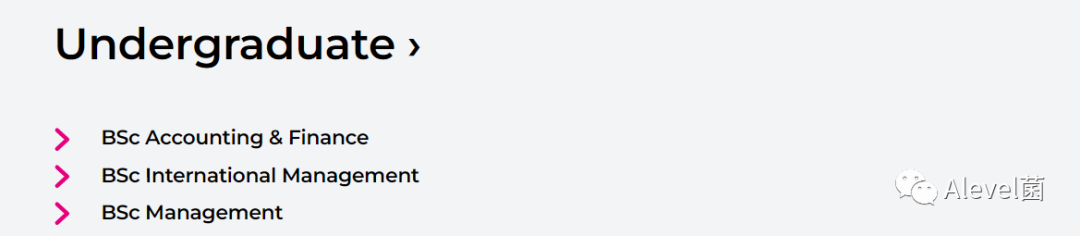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