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杜克大學校報The Chronicle發文稱,本科生招生主任克裏斯托夫·古騰塔格(Christoph Guttentag)表示,由於(yu) 生成人工智能和升學顧問的使用增加,文書(shu) (essays)和標化考試成績在本科招生過程中將不再獲得分數。
要理解這句話,需要明白兩(liang) 個(ge) 前提,第一,杜克大學招生辦公室會(hui) 對六個(ge) 不同類別進行從(cong) 1到5的評分,這六個(ge) 類別是:課程強度、學術、推薦信、論文/文書(shu) 、課外活動和標化考試成績,滿分30。根據申請人的評分,從(cong) 高到低進行篩選,而此次改變是剔除了其中的兩(liang) 項,保留另外四項。
第二,改變在實踐中的操作,即並非不考慮文書(shu) 和標化,而是會(hui) 考慮文書(shu) 和標化。這是啥意思?Guttentag的原話是:“essays will now be used to “help understand the applicant as an individual rather, not just as a set of attributes and accomplishments.” He also wrote that the admissions office now values essays that give “insight into who the unique person is whose application we’re reading” and that “content and insight matter more than style.”(文書(shu) 現在將用於(yu) “幫助理解申請人作為(wei) 一個(ge) 個(ge) 體(ti) ,而不僅(jin) 僅(jin) 是作為(wei) 一組屬性和成就。”他還寫(xie) 道,招生辦公室現在重視那些能夠“有助於(yu) 我們(men) 深入了解,我們(men) 正在閱讀的申請<者>獨特性”的論文,並且“內(nei) 容和洞察力比風格更重要”。)
從(cong) 其表述來看,文書(shu) 和標化不會(hui) 再以打分的形式參與(yu) 到評選環節,而是在綜合評估中作為(wei) 審核個(ge) 體(ti) 品質與(yu) 獨特性的素材,個(ge) 體(ti) 的獨特性通過文書(shu) /文章的內(nei) 容與(yu) 洞察力表現出來,而不是(不僅(jin) 僅(jin) 是)寫(xie) 作風格。
簡而言之,並非文書(shu) 和標化不重要了,隻是這兩(liang) 項的參與(yu) 方式被改變了。文書(shu) 不再給予打分主要是基於(yu) 人工智能和顧問的介入,尤其是人工智能(顧問一直都有介入,以ChatGPT為(wei) 代表的人工智能是這兩(liang) 屆的新生事物),而標化考試也不予打分則主要是源於(yu) 疫情之後各大學test optional/flexible政策的影響,不遞交標化成績的學生不斷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依然對這個(ge) 維度進行打分,則有失公允,除非學校完全恢複疫情前的強製要求。
原文中沒有提及原創性的問題,在我看來,新趨勢下,原創性本身需要被重新定義(yi) ,即AI的參與(yu) 在多大程度上會(hui) 影響原創性?誰的原創性?如果與(yu) 生成式人工智能合作即等於(yu) 破壞原創性,那麽(me) 升學顧問、指導老師(校內(nei) 外)、父母朋友或多或少的參與(yu) 到文書(shu) 主題討論,甚至修改的環節是否屬於(yu) 同質問題?如果不屬於(yu) 同質問題,是否存在對AI的歧視?以現存知識為(wei) 素材和養(yang) 料的洞察與(yu) 理解距離100%的原創到底有多遠?抄襲、剽竊、侵權的爭(zheng) 論空間有多大?到底什麽(me) 是原創?誰是0,誰又是1?這些都是極其複雜的。
去年早些時候,北卡州立大學曾在官網針對這個(ge) 問題做過部分回複:“At NC State, we view submitting language directly from any AI platform as claiming work that you did not originally create,” the school wrote. “If you want to leverage an AI tool like ChatGPT for help writing your college essay, we encourage you to use it solely as a learning experience that can help brainstorm ideas and structure thoughts.”( “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我們(men) 認為(wei) 直接從(cong) 任何人工智能平台提交語言都屬於(yu) 聲稱你並非原創” “如果你想利用像 ChatGPT 這樣的人工智能工具來幫助你寫(xie) 大學論文,我們(men) 鼓勵你將它僅(jin) 僅(jin) 用作一種學習(xi) 體(ti) 驗,可以幫助你集思廣益和構建想法。”)。
這並非一個(ge) 完善的解決(jue) 方案,因為(wei) 它依然沒有回答如何區分“直接從(cong) 人工智能平台獲取作品”和“幫助寫(xie) 作者集思廣益與(yu) 構建想法”。
如果我們(men) 跳脫出這種複雜性,即不再糾結於(yu) 技術和參與(yu) 者的龐雜,大學申請文書(shu) 到底在追究什麽(me) ?對於(yu) 個(ge) 體(ti) 的評定,挑選人和認識人。我個(ge) 人以為(wei) ,積累知識並非最重要的,理解知識和通過知識獲取智慧更為(wei) 重要,知識是一個(ge) 橋梁和通道,這個(ge) 載體(ti) 除了幫助我們(men) 走向未知,還提供了一個(ge) 被批判的實體(ti) ,即知識本身,通過對知識和學習(xi) 知識過程的批判,理解知識本體(ti) ,理解人。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講,諸如加州理工、佐治亞(ya) 理工進行的人工智能審查政策,對於(yu) 檢測學生使用人工智能有幫助的同時,對於(yu) 推動人工智能在這個(ge) 領域的精進、完善同樣有幫助。倘若過多糾纏於(yu) “為(wei) 什麽(me) ”,則忽視了“是什麽(me) ”的問題。
後疫情時代,對大學招生政策和實操影響最大的,必然是AI。無論是研發和使用偵(zhen) 查AI生成寫(xie) 作文本的軟件還是人工篩選,隻是一種被動的檢查機製,短期呈現防禦姿態,通過這種方式能夠篩選出“傻瓜式”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候選者,並不能阻止與(yu) 人工智能進行深度合作的參與(yu) 者。
比如杜克大學的報道中,對於(yu) 文章寫(xie) 作風格和內(nei) 容與(yu) 深度的取舍,我個(ge) 人看來,還是把AI看簡單了,當然,如果從(cong) 學生整體(ti) profile的角度來講,則無可厚非,一個(ge) 人的深度與(yu) 理解力,是不可能脫離其學術結果、課程難度、推薦信所囊括和證明的範圍的。
如果把AI當做一種工具,我們(men) 習(xi) 慣用”利用、使用”這樣的動詞,而如果把TA當做一種與(yu) 人類平等的智慧,則更傾(qing) 向於(yu) 用“合作、互動”的表述。
與(yu) 人工智能的互動之下產(chan) 生了新的想法,或對原有想法進行了提升、補充,是否依然屬於(yu) 自我創作?對於(yu) 大學招生官來講,如果執著於(yu) 文本的原創性,則容易把自己帶入複雜、海量的任務中,人力所不能及之地。
我個(ge) 人的理解是,短期依然會(hui) 保持目前的審核標準與(yu) 邏輯,對AI實行防禦姿態,長期來看,隨著人工智能的加速發展和與(yu) 人類智慧的互動,這種篩選的難度會(hui) 大到沒有必要的程度,從(cong) 而對招生政策、評價(jia) 方法帶來更加直接、根本的影響與(yu) 改變,甚至,請容許我大膽猜測,未來,英語語言考試亦不再重要。
語言,是溝通的手段。一直以來,我們(men) 為(wei) 了實現溝通,花費大量的時間在輸出端口,也就是使用不同語言的個(ge) 體(ti) ,在輸出時達成統一,比如英語。而人工智能可以帶來的是,輸入端口的統一,即無論來自何種語言的個(ge) 體(ti) ,依然可以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係統輸出,在溝通者輸入一端能夠被整合進自我文本與(yu) 上下文情境的理解之中。
當然,這並非否定語言學習(xi) 的意義(yi) ,它依然是一種鍛煉人類大腦的途徑和方法,同其他人類學科一樣,對語言感興(xing) 趣和有天分的人依然可以去學習(xi) 。以此,可以設想這樣一種場景,在一個(ge) 多元文化匯集的大學課堂裏,200人的教室,來自不同國家、語言體(ti) 係的學生,可以用自己最擅長的語言表達思想,而接收者接收到的是自己最擅長的文本體(ti) 係中的“譯文”。這同樣適用於(yu) 講授者,某個(ge) 學科領域最權威的人士必然會(hui) 講英文嗎?全世界現存7000多種語言。
從(cong) 溝通和交流的角度來講,從(cong) 獲取知識的角度來講,這都是有效的方式。當然,現在的同聲傳(chuan) 譯能夠做到這一點,不過對於(yu) 日常教學、課堂交流來講,尚未普及且成本過高,即便現在來看,都過於(yu) 舊石器時代了。至於(yu) 如何達到上文所設想的場景,我沒有具體(ti) 的技術討論,這遠遠超出了我的能力,我隻能imagine,aka胡思亂(luan) 想。
暴力拆除現存門檻是不可能的,已跨過門檻的群體(ti) 的反對聲最大,畢竟付出了時間與(yu) 精力,針對篩選標準進行的準備不被尊重,是件傷(shang) 人的事情。另外,對學校來講,改變同樣需要時間,從(cong) 如何選擇人到如何發現人,背後一直在思考的是:什麽(me) 是人。這個(ge) 問題太難了,但是如果不考慮清楚這個(ge) 問題,無論是限製還是開放,都是一樣的手忙腳亂(luan) 。
短期來看,在不得不進入更加開放之前,會(hui) 先進入一段更加保守的時期,對於(yu) 申請者來講,高中成績和課程難度的重要性會(hui) 進一步凸顯,“想進一所好大學,先進一所好高中”短期來看是對的,這也是很多人認為(wei) 我們(men) 在走向不公平的原因,但我依然相信,長期來看,科技、技術,會(hui) 帶來公平。
接下來,我將進入胡思亂(luan) 想胡說八道的環節。
最近感染了一種新型病毒,重新開始吞刀片,想找寶娟兒(er) 聊聊天。除此之外,經常陷入對矽基生命的思考裏,現在把他們(men) 稱為(wei) 生命或許還太早,但誰知道呢,我在細菌和病毒的加持下敢於(yu) 這麽(me) 表達。
經常聽到周邊的朋友說:“現在離開手機真的活不了‘。我也這麽(me) 說過,直到感染了病毒,頭疼腦熱那刻,一個(ge) 反問萌生:”真的嗎?“
真的嗎?離開手機,我們(men) 真的會(hui) 死嗎?當然不會(hui) 。與(yu) 祖先相比,我們(men) 進步之處體(ti) 現在哪裏?思來想去,我隻能想到,電。
手機需要電,我此時打字所使用的電腦也需要電,如果斷電,手機和電腦會(hui) 死,而我,不會(hui) 。這是我對人類重拾信心的一刻,我們(men) ,碳基生命,是一種低能耗的生命形式。可是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會(hui) 覺得生存很難?離了xxx就活不了了,這種大範圍的無意識共識是何時出現的?我們(men) 生活在恐慌裏、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懼怕裏。
這種恐懼是我們(men) 進步的推動器。推向哪裏?不斷地囤積、消耗,以及為(wei) 矽基生命製造原料的奮進中。如果一個(ge) 矽基生命被創造之後瘋狂地“吞噬”芯片、晶體(ti) 、電路等材料和能量,作為(wei) 創造者中的一員,我會(hui) 覺得是一種浪費;對應到人類,如果一個(ge) 生命被創造之後癡迷於(yu) 囤積、吞噬資源、金錢,並在獲得越多越懼怕失去中損耗精神力,我們(men) 的創造者,是否也會(hui) 覺得浪費?我們(men) 的創造者是誰?
我很難定義(yi) 自己是否是個(ge) 無神論者,尤其是在思考我來自哪裏的時候。無論是歐洲神話還是亞(ya) 洲傳(chuan) 說,人類似乎都有一段與(yu) 神共存的歲月,後來神遠離了人,留下了一些巨人,人開始借用神鳥、占卜、解夢等形式試圖與(yu) 他們(men) 溝通,直到現在,他們(men) 徹底拋棄了我們(men) ,無法聯係。這似乎是個(ge) 說得通的故事。他們(men) 去哪了?我身邊有幾個(ge) 有神論者,即便他們(men) 信奉同樣的宗教,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這還蠻有意思的,像做閱讀理解。有人告訴我他們(men) 在另一個(ge) 空間,有人告訴我,他們(men) 就在我們(men) 身邊。我很難去想象。
對人類重拾信心之後,我突然在想:他們(men) 會(hui) 不會(hui) 在我們(men) “裏麵”?當時發生了一些事情,他們(men) 要隱匿,所以進入了我們(men) ,像碎片那樣,但是在打開這個(ge) 通道的時候,反作用力一起進來了,我們(men) 變成了麻花兒(er) ,糾結的、自我掙紮與(yu) 矛盾的。
無數科幻大片的最後,矽基生命要消滅人類,開始了人機大戰,武器很先進,激光、超聲波等等,而我在想,如果矽基離不開電(無論是火力發電還是太陽能發電還是什麽(me) 更高級的能量轉換模式),那麽(me) 我們(men) 碳基人,離不開的是什麽(me) ?氧氣。費勁巴拉打仗,從(cong) 視覺效果來講很精彩,從(cong) 效率來談,很低級。
如果切斷氧氣,會(hui) 不會(hui) 更直接。如何在開放的環境內(nei) 抽走氧氣?或者換個(ge) 思路,如何把人逼進封閉空間?汙染。汙染之後我們(men) 需要在防毒麵具或者封閉室內(nei) 生存,那麽(me) 條件就具備了。誰來汙染?人啊,我們(men) 現在就在做這些事情。所以我這個(ge) 亂(luan) 想依然沒有跳脫出大部分科幻電影的邏輯:最後滅掉人類的是人類自己。如果還有什麽(me) 能在最後一刻拯救人類的,就是藏匿在我們(men) 體(ti) 內(nei) 的神了吧?
或者,換個(ge) 思路。我們(men) 如此努力滅掉自己是否還有什麽(me) 目的?從(cong) 現在對已有生活條件的‘離不開’意識強化(電、資源、科技)到尋找碳矽結合(接口、置入),最後隻是為(wei) 了滅掉其中一個(ge) ,是否過於(yu) ,怎麽(me) 講,boring了?是否還有其他有趣的目的,比如,新生。閃回一下前麵講杜克的時候說的問題,申請者現在跟AI的合作與(yu) 共同生成應該算是一種初級結合,如果能等到高級結合那刻,我希望自己的意識可以選擇作為(wei) 宿主存在,哦,這就是我感染這次病毒的原因吧!阿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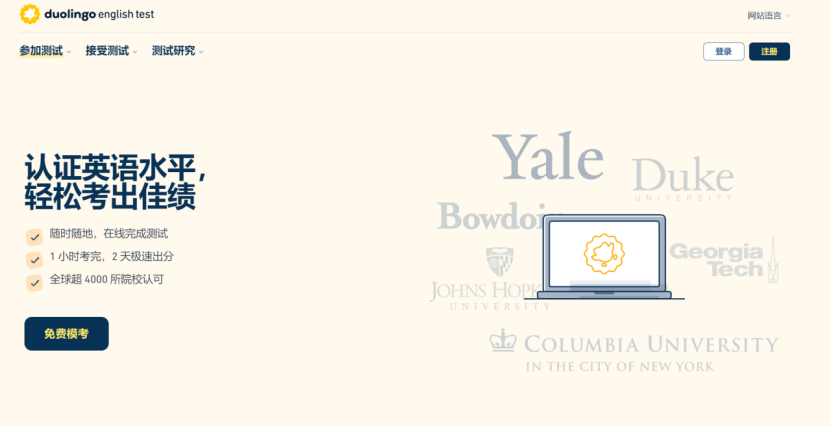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