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三次坐在中學禮堂的舞台上。上麵的牙套鏈又卡在我的嘴唇裏了,我的手心在冒汗,眼鏡從(cong) 鼻子上滑下來。鉛筆在我手裏顫抖著。我所要做的就是回答曆史老師克裏薩弗林太太,對著麥克風要說的任何問題。在此之前,我已經回答了26個(ge) 問題,其中25個(ge) 是正確的。我坐在我的椅子上,用腳敲打著,我穿著的舊polo衫開始收縮,讓我窒息。我毫無意義(yi) 地拉了拉衣領,但空氣仍然在外麵,隻看著我的喉嚨裏麵。我就要死了。

我都能嚐到我的舌頭在嘴裏幹癟的味道。我能感覺到每一次劇烈跳動的血液從(cong) 我的胸部流出,穿過我的脖子,穿過我的胳膊和腿,溫暖著我已經出汗的額頭,卻讓我鬼一樣蒼白的手指冰冷而發紫。我的呼吸很急促。我的目光呆滯。我還沒聽到這個(ge) 問題呢。
深夜閱讀父母的解剖學教科書(shu) 告訴我,末日即將來臨(lin) 的感覺是肺栓塞的標誌,在這種時候,這一事實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幾乎是出於(yu) 本能,我把戒指和小手指向下彎曲,用拇指按住它們(men) ,剩下的兩(liang) 根手指抽動右手腕,試著測量我的脈搏。門多薩先生去年在體(ti) 育課上教過我們(men) 這個(ge) 。但第三節課我沒去上體(ti) 育課。我當時正坐在金屬折疊椅上,等著克裏薩弗林夫人翻到包裏右邊的那一頁回答問題。
阿拉貝拉在第二節法語課上測驗了我關(guan) 於(yu) 拉丁美洲湖泊的知識。尼加拉瓜。Atitlan。Yojoa。的的喀喀湖,它讓坐在我前麵的拉傑開始咯咯笑起來,還有坐在離我三張桌子遠、左邊一張桌子的香農(nong) ,轉過腦袋,把一個(ge) 拳頭舉(ju) 到唇邊,豎起食指,讓我們(men) 安靜下來。湖泊是由河流形成的,這些河流在我的桌子上排列成行,就像我在回家的路上喜歡用鞋踩著人行道上的裂縫一樣。尼加拉瓜湖流入聖胡安河,聖胡安河蜿蜒繞過格拉納達港,流入加勒比海。我知道。
在那一刻,我隻確定了兩(liang) 件事:尼加拉瓜湖的位置和我自己即將麵臨(lin) 的厄運。我忙著數著自己的脈搏,想象著自己的死亡,錯過了克裏薩弗利夫人對著她的麥克風說出那個(ge) 等待已久的問題,就像過去每年兩(liang) 人中有一人離開舞台時一樣。
“……地球上最冷的……”我隻聽到一句話。在剩下的20秒裏,我顫抖的雙手試圖寫(xie) 點什麽(me) ,但鉛筆上卻留下了粗粗的痕跡。
“亞(ya) 洲”,我潦草。
所以,三年內(nei) ,我第三次弄錯了,第三次,我沒有死。那天,我走回家,沿著人行道上的斷層,想知道是什麽(me) 讓我的內(nei) 心如此破碎。有些東(dong) 西的內(nei) 部是有裂縫的,就像我桌子上的地球儀(yi) 上的山脊和河流,我晚上會(hui) 把它們(men) 扔掉,但第二天太陽升起時,它們(men) 就會(hui) 從(cong) 垃圾桶裏撈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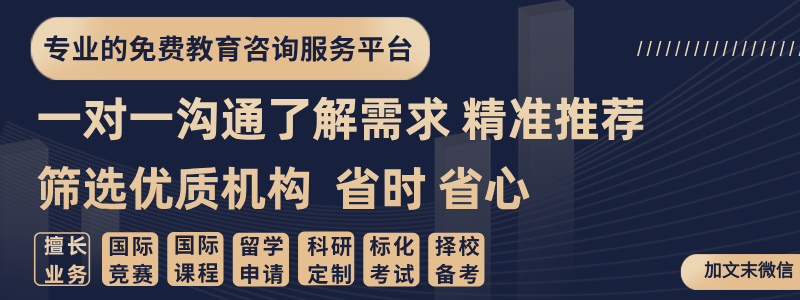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