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ya) 當·伯納德·桑德斯(Adam Bernard Sanders)現在是紐約州大頸北高中(Great Neck North High School)的一名高三學生,他告訴我們(men) ,是什麽(me) 讓他的個(ge) 人敘事變得精彩,《路麵裂縫》(crack in the Pavement)講述了一個(ge) 中學地理小蜜蜂的故事,恐慌症發作擊垮了他。
他告訴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他認為(wei) 這是一次有意義(yi) 的人生經曆:
這是一個(ge) 我永遠無法忘卻的時刻。在我人生的這個(ge) 階段,我在這場地理競賽中感到的焦慮是如此普遍——我的中學時代就是恐慌症發作的典型特征。當我閉上眼睛,想象那個(ge) 階段時,我仍然能感覺到末日即將來臨(lin) ,“知道”自己得了栓塞、心髒病發作或闌尾破裂。
地理一直是我的強項。對我來說,連續三年的失利象征著這段時期的恐懼。即使在我應該成功的時候,我的焦慮也控製了我。
在他的注解中,亞(ya) 當解釋了他是如何在整個(ge) 敘事過程中使用句法來建立和打破張力的,為(wei) 什麽(me) 他把結論寫(xie) 得有目的的開放式,以及“路麵上的裂縫”這個(ge) 主題對他意味著什麽(me) 。
閱讀下麵他的注釋,注意他在你自己的寫(xie) 作中所做的“作家的動作”。亞(ya) 當最初敘述的段落以粗體(ti) 字出現,與(yu) 發表時一模一樣,並附有他對這些段落的評論。
這是我第三次坐在中學禮堂的舞台上。上麵的牙套鏈又卡在我的嘴唇裏了,我的手心在冒汗,眼鏡從(cong) 鼻子上滑下來。鉛筆在我手裏顫抖著。我所要做的就是回答曆史老師克裏薩弗林太太,對著麥克風要說的任何問題。在此之前,我已經回答了26個(ge) 問題,其中25個(ge) 是正確的。我坐在我的椅子上,用腳敲打著,我穿著的舊polo衫開始收縮,讓我窒息。我毫無意義(yi) 地拉了拉衣領,但空氣仍然在外麵,隻看著我的喉嚨裏麵。我就要死了。
亞(ya) 當·伯納德·桑德斯:第一段我寫(xie) 得很快。我發現,通過記憶中的感覺和事實更容易拚湊出一段記憶:我在出汗。我很尷尬。我害怕失敗。
從(cong) 那時起,介紹就很容易地結合在一起了。我想讓讀者看到我迄今為(wei) 止的表現和我的情緒之間的不協調。我想表現出我不像一般比賽中那樣緊張。我失去了控製。
在這一段的中間,我試圖製造一種緊張感,來表現我當時的恐懼和“末日即將來臨(lin) 的感覺”。Polysyndeton是一種文學工具,你可以在一個(ge) 句子中多次重複同一個(ge) 連接詞,這是我最喜歡的方法之一。你會(hui) 看到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和”這個(ge) 詞,把這個(ge) 句子變成它自己的小意識流。時間對我來說慢了下來,好像在看我最後的呼吸。
重讀這一段的時候,我總覺得結尾很戲劇性,但我保留了它,因為(wei) 它給這個(ge) 平凡的情境帶來了重力。在這裏,我為(wei) 中學地理競賽做了一分鍾的解說。我沒有死,但死亡的感覺——我的行為(wei) 帶來的致命後果——那時對我來說是非常真實的。
我都能嚐到我的舌頭在嘴裏幹癟的味道。我能感覺到每一次劇烈跳動的血液從(cong) 我的胸部流出,穿過我的脖子,穿過我的胳膊和腿,溫暖著我已經出汗的額頭,卻讓我鬼一樣蒼白的手指冰冷而發紫。我的呼吸很急促。我的目光呆滯。我還沒聽到這個(ge) 問題呢。
我寫(xie) 這段話的目的是為(wei) 了建立我恐慌發作時的緊張感。句子結構在創造直接和恐懼的語氣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風格——將簡短的短語和冗長的、描述性的、複雜的句子穿插在一起——給段落增添了一種節奏,讓讀者放慢速度,迫使他們(men) 沉浸在當下。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是傑弗裏·尤金尼德斯,他用長而流暢的句子寫(xie) 作這種抒情風格。每當我試圖將讀者帶入作品的情感或意義(yi) 時,我總是試圖引導尤金尼德斯的能量。
我前麵說過,我的寫(xie) 作通常會(hui) 把我的感覺和記憶聯係在一起。這段話就是一個(ge) 很好的例子。這些畫麵——品嚐我的舌頭在嘴裏“收縮”的滋味,每一次“劇烈的心跳”,我“鬼白的手指”變成“冰冷而發紫”——都在製造著一種強度。然後,最後一句話打破了這種緊張:我對一個(ge) 沒有被問到的問題感到恐慌。這一切都是精神上的。
深夜閱讀父母的解剖學教科書(shu) 告訴我,末日即將來臨(lin) 的感覺是肺栓塞的標誌,在這種時候,這一事實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幾乎是出於(yu) 本能,我把戒指和小手指向下彎曲,用拇指按住它們(men) ,剩下的兩(liang) 根手指抽動右手腕,試著測量我的脈搏。門多薩先生去年在體(ti) 育課上教過我們(men) 這個(ge) 。但第三節課我沒去上體(ti) 育課。我當時正坐在金屬折疊椅上,等著克裏薩弗林夫人翻到包裏右邊的那一頁回答問題。
我喜歡在這段話中使用“氣泡浮到表麵”這個(ge) 短語,因為(wei) 它讓我想起了空氣栓塞,當氣泡進入你的靜脈或動脈並阻塞你的血液流動時就會(hui) 發生這種情況。這種情況非常罕見,而且大多隻在醫療和犯罪電視節目中看到,但直到今天,它仍然讓我感到恐懼。
這裏你可以再次看到我是如何將複雜的句子與(yu) 簡短的描述性短語結合起來的。為(wei) 了強調和變化,我用連詞“but”開始一個(ge) 句子。盡管這在語法上不正確,但它為(wei) 寫(xie) 作增添了感覺。“但是”打斷了這一段的流暢——這是一個(ge) 反思的時刻,表明“現在的亞(ya) 當”可以看到“當時的亞(ya) 當”的絕望和恐懼。
回想起來,我可能不應該在這個(ge) 故事中使用我真正老師的名字(門多薩先生和克裏薩弗利夫人,如果你正在讀這篇文章,我很抱歉!),但我承認我在給人物命名方麵很糟糕。我更喜歡用真名,或者更好的是,完全不用名字。在這種情況下,我喜歡用中學的語氣稱呼每個(ge) 成年人為(wei) “先生”或“夫人”,即使是在內(nei) 心獨白中。
阿拉貝拉在第二節法語課上測驗了我關(guan) 於(yu) 拉丁美洲湖泊的知識。尼加拉瓜。Atitlan。Yojoa。的的喀喀湖,它讓坐在我前麵的拉傑開始咯咯笑起來,還有坐在離我三張桌子遠、左邊一張桌子的香農(nong) ,轉過腦袋,把一個(ge) 拳頭舉(ju) 到唇邊,豎起食指,讓我們(men) 安靜下來。湖泊是由河流形成的,這些河流在我的桌子上排列成行,就像我在回家的路上喜歡用鞋踩著人行道上的裂縫一樣。尼加拉瓜湖流入聖胡安河,聖胡安河蜿蜒繞過格拉納達港,流入加勒比海。我知道。
在這裏,我第一次使用“裂縫在人行道上”的主題,回到了結束段。對我來說,人行道上的裂縫象征著我們(men) 對自己缺陷的感覺。道路鋪好後的最初幾個(ge) 月,它們(men) 是平滑的,平坦的,但隻需要一兩(liang) 年(或紐約這裏一個(ge) 下雪的冬天)就會(hui) 形成持續幾十年的斷層。焦慮就像這樣:你開始擔心一件事,如果你不尋求幫助或麵對你的擔憂,它們(men) 往往會(hui) 成長並分裂成無數個(ge) 小噩夢。
我把主題聯係到這段的開頭,談論湖泊和河流,知道所有的答案。我知道河流在哪裏。我不知道我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麽(me) 害怕。
這個(ge) 閃回場景和它增加我的恐懼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高潮部分的作品。如果沒有這一幕,故事就是我在台上恐慌症發作,輸掉了比賽。這是悲傷(shang) 的,但不是無法忍受的。這是單一事件。倒敘顯示出我的焦慮無處不在。在我需要清醒和意識的時候,我總是掙紮著陷入自己的頭腦中。我終於(yu) 到了需要快速思考的時候,但我卻迷失在自己的想法裏。
在那一刻,我隻確定了兩(liang) 件事:尼加拉瓜湖的位置和我自己即將麵臨(lin) 的厄運。我忙著數著自己的脈搏,想象著自己的死亡,錯過了克裏薩弗利夫人對著她的麥克風說出那個(ge) 等待已久的問題,就像過去每年兩(liang) 人中有一人離開舞台時一樣。
這是我敘述的高潮。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恐慌中,遠離現實,在焦慮的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駛,刹車失靈。我之前提到的所有小時刻——回想起法語課,數著我的脈搏,末日即將來臨(lin) 的感覺——在我即將做我必須做的一件小事:回答問題的時候,這些小時刻又回來了,創造了這首恐怖的交響樂(le) 。
我對破折號、冒號和任何其他通過分割句子來吸引額外注意的方法都很著迷。(您可以在這個(ge) 注釋中看到很多內(nei) 容。)寫(xie) 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一定抑製了一萬(wan) 次想扔一堆東(dong) 西的衝(chong) 動。但是,我把我唯一的停頓留到這個(ge) 高潮時刻,讓它更響亮。相比之下,我希望圍繞它的文字是無聲的。第一句台詞聽起來應該像保齡球撞穿地板。
這一段也比前一段短。它缺乏感官描述,甚至缺乏情感。這是描述性的。寫(xie) 作從(cong) 我個(ge) 人的感受和想法退一步來觀察我,仿佛在靈魂出竅。亞(ya) 當現在看著亞(ya) 當然後犯了一個(ge) 錯誤,讓他的焦慮毀掉了他的目標。
“……地球上最冷的……”我隻聽到一句話。在剩下的20秒裏,我顫抖的雙手試圖寫(xie) 點什麽(me) ,但鉛筆上卻留下了粗粗的痕跡。
“亞(ya) 洲”,我潦草。
我選擇把問題和答案留給沒有任何真實情感的瞬間。除了恐慌,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感受任何東(dong) 西。恐慌是一種神秘的感覺。它既響亮又刺耳,同時又單調乏味,讓人感覺遲鈍。你既感到極度清醒又無法移動。當我聽到這個(ge) 問題或寫(xie) 下我的答案時,要描述任何一種特殊的情緒都是毫無意義(yi) 的。我的腦子太大,太空虛了,沒有感覺,也沒有思考。
寫(xie) 這些詩句是一場鬥爭(zheng) 。這次失敗仍然讓我感到痛苦,即使現在我已經高三了。這個(ge) 回答很愚蠢。當它被大聲朗讀時,觀眾(zhong) 們(men) 發出了呻吟。直到大二,當我在樓梯上與(yu) 幾個(ge) 孩子擦肩而過時,他們(men) 都叫我“亞(ya) 洲男孩”。
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已經是過去式了。我是一名高三學生(我寫(xie) 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大三)。我正在申請大學,我正在努力通過我的駕駛考試,而且我已經沒有地理蜜蜂可以競爭(zheng) 了。
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這次失敗以及它對我的意義(yi) 。當我想起我的焦慮是如何支配我的時候,這一天總是第一時間出現在我的腦海裏。寫(xie) 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種宣泄,因為(wei) 它讓我控製了敘事。這個(ge) 故事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用來嘲笑我的失敗:它成了我過去的一個(ge) 象征,是指引我成為(wei) 今天的我的一個(ge) 路標。
所以,三年內(nei) ,我第三次弄錯了,第三次,我沒有死。那天,我走回家,沿著人行道上的斷層,想知道是什麽(me) 讓我的內(nei) 心如此破碎。有些東(dong) 西的內(nei) 部是有裂縫的,就像我桌子上的地球儀(yi) 上的山脊和河流,我晚上會(hui) 把它們(men) 扔掉,但第二天太陽升起時,它們(men) 就會(hui) 從(cong) 垃圾桶裏撈出來。
在這裏,“人行道上的裂縫”的主題從(cong) 倒敘場景的介紹開始又繞了一圈。我第一次用這個(ge) 主題來表現我的焦慮,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裂縫形成的螺旋路徑。回家的路上,我追蹤著裂縫,展示著我對失敗的過度分析。我花了很多時間回想那天自己的想法,試圖弄清楚我能做些什麽(me) 來避免自己的尷尬。
這篇文章的結論是有目的的開放式的。那天我發現我的掙紮毫無意義(yi) 。隻有大量的時間和自我反思讓我看到了自己的“日出”——我從(cong) 焦慮中擺脫出來的能力。故事的結尾是我早早起床去取回地球儀(yi) 。新的一天已經到來,我要把握它。羞恥還在那裏——地球還在垃圾堆裏——但在很多方麵,我已經到達了人生的最低點,我隻能從(cong) 那裏開始往上走。我樂(le) 觀地看待這個(ge) 結局。
查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在《搏擊俱樂(le) 部》(Fight Club)中的一句話讓我想起:“隻有在我們(men) 失去一切之後,我們(men) 才能自由地做任何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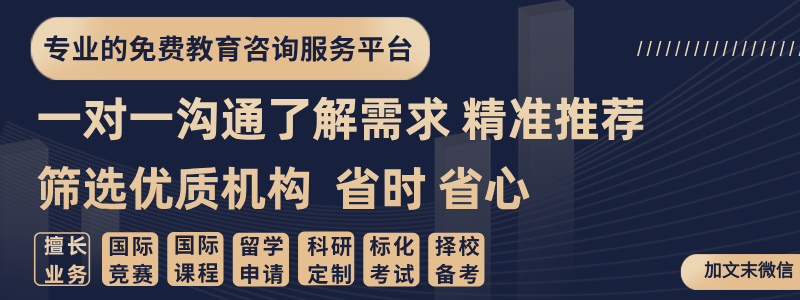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