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年,我們(men) 邀請了 11 至 19 歲的學生為(wei) 我們(men) 的個(ge) 人敘事寫(xie) 作比賽講述關(guan) 於(yu) 有意義(yi) 的生活經曆的簡短而有力的故事。第三年,我們(men) 從(cong) 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那裏聽到了塑造他們(men) 今天的大大小小的時刻:未能達到期望的初吻,導致自我接受的學校作業(ye) ,機場安檢事件讓世界看起來不那麽(me) 甜蜜,甚至更多。
我們(men) 的評委閱讀了超過 11,000 份提交的作品,並選出了 200 多名決(jue) 賽選手——8 名獲勝者、16 名亞(ya) 軍(jun) 、24 篇榮譽獎和 154 篇進入第 4 輪的論文——他們(men) 的故事讓我們(men) 感動,讓我們(men) 思考、歡笑和哭泣。“我總是被這些故事中的脆弱和溫柔所震撼,”一位法官評論道。
下麵,您可以閱讀全文發表的八篇獲獎論文。

內(nei) 疚
作者:Lyat Melese,16 歲,弗吉尼亞(ya) 州亞(ya) 曆山大市托馬斯傑斐遜科技高中
尖銳的哨聲劃過體(ti) 育館,慢慢地停止了彈跳的籃球、吱吱作響的網球鞋和背景的喋喋不休。我的體(ti) 育老師站在教室中間,厭惡地環顧四周,看著淩亂(luan) 的籃球、呼啦圈和排球網。他要求誌願者幫助清理體(ti) 育館。
Saanvi 將一隻手舉(ju) 到空中。其他人都拒絕看老師的眼睛,專(zhuan) 注於(yu) 地板、他們(men) 的手或天花板。
當它再次響起時,我歎了口氣。
伊隆塔
很難用英語定義(yi) 阿姆哈拉語單詞。它描述了一種由極端同理心和無法說“不”的混搭而成的感覺。這是我在母親(qin) 身上看到的一種特質,令我煩惱的是,我自己也看到了這種特質。雖然yilugnta讓我在家裏成為(wei) 一個(ge) 善良和受人尊敬的女兒(er) ,但它讓我在學校裏容易被內(nei) 疚絆倒。
我舉(ju) 起手,“我能行。”
Saanvi 和我收集了所有的球和繩索,將手推車推入儲(chu) 藏室。
當她突然停下來看著我時,我們(men) 獨自一人。
“你被錄取了嗎?” 她問,指的是當地 STEM 高中的高度選擇性錄取。
“是的,”我回答。“你?”
她移開視線。她的雙手攥緊身側(ce) ,眉頭緊鎖在她的臉上。
我往下看。“對不起。我知道你有多想去。”
“你不明白,”她吐了出來。“你顯然是因為(wei) 你是黑人才進來的。”
我沒有回應,而是專(zhuan) 注於(yu) 我堆成一堆的彩色呼啦圈:綠色、黃色、藍色。
當我們(men) 第一次搬到美國時,我的父母竭盡全力避免使用“黑人”這個(ge) 詞。他們(men) 向我灌輸我不僅(jin) 僅(jin) 是黑人,我是埃塞俄比亞(ya) 人。我曾經認為(wei) 這是因為(wei) 他們(men) 不想讓我忘記我的文化。現在我認為(wei) 他們(men) 在保護我,因為(wei) “黑人”這個(ge) 詞肩負著曆史的重任。
我的尼日利亞(ya) 鄰居在看尼日利亞(ya) 新聞時總是咬著牙自言自語。他指責英國強迫部落聚集在一起。他說尼日利亞(ya) 不應該存在。現在,他的妻子因為(wei) 血壓過高而把遙控器藏了起來。
我媽媽的朋友的非洲裔美國伴侶(lv) 每周都會(hui) 去市政廳抗議。他仍在等待他的祖先得到賠償(chang) 的那一天。
我媽媽告訴我,我們(men) 不像他們(men) 。我們(men) 的祖先沒有被殖民或奴役。不要背負不屬於(yu) 你的負擔。
在我的腦海裏,我想尖叫我沒有選擇攜帶任何東(dong) 西。它被鏟到我的頭頂上。就像我的yilugnta一樣,這是我必須擁有的特質,不管我多麽(me) 希望。
桎梏和爭(zheng) 奪土地的時代早已過去,但餘(yu) 波回蕩在我們(men) 耳邊,耳語如“受害者”、“捕食者”和“多元化雇傭(yong) ”。
黑是黑是黑。
我轉身看著Saanvi。
“招生是不分種族的,”我說。
“每個(ge) 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她嘲笑道。“這麽(me) 少的黑人申請,你肯定有一個(ge) 名額。”
她推開我的肩膀,大步走出房間。
她的包被遺忘在地板上,前麵掛著一個(ge) 鑰匙鏈,上麵掛著一個(ge) 五顏六色的和平標誌。
我盯著它,打算把它放在那裏。
伊隆塔
我拿起肩帶,把它扛在肩上,再次背負著我不屬於(yu) 自己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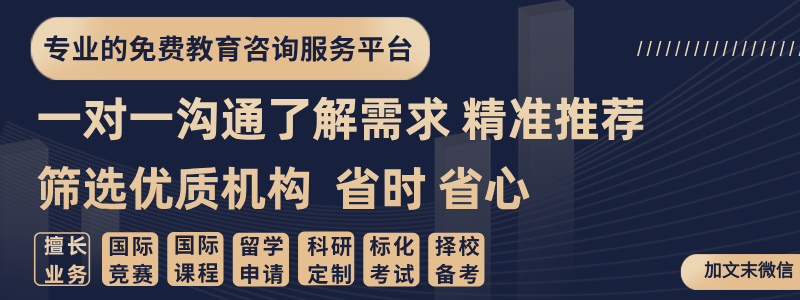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