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電話終於(yu) 不再響了,整個(ge) 房子都沉浸在悲傷(shang) 中,我讓家裏充滿了酥皮和甜桃子的香味,來掩蓋仍然縈繞不去的擔憂的氣味。
在確診後的那個(ge) 周末,媽媽給每個(ge) 關(guan) 心她的親(qin) 戚、老朋友和大學室友都複製粘貼了同樣的文字:傑伊在4月份被診斷出患有一種早發性癡呆。上周我們(men) 約了休斯頓的一位神經學家。他的情況被稱為(wei) 皮克病。我們(men) 將在幾周後回來獲取更多信息。

然後媽媽放下電話,揉了揉額頭,建議我們(men) 開車去兜風。
爸爸的卡車被公司沒收後,我們(men) 從(cong) 鄰居那裏買(mai) 了一輛日產(chan) 探路者。在州際公路上,我們(men) 經過了一條飄揚的橫幅,上麵寫(xie) 著醒目的紅色字母:“弗雷德裏克斯堡桃子,你能找到的德克薩斯州中部最好的水果。”媽媽戴上醫用口罩,去和小販討價(jia) 還價(jia) 。
現在在我們(men) 的廚房裏,桃子汁通過紙盒滲到櫃台上。我在水槽下麵衝(chong) 洗了一個(ge) 成熟的桃子,把它舉(ju) 到嘴邊。果汁順著我的下巴滴到我的胳膊上。甜甜的香味彌漫到客廳,把爸爸從(cong) 電視上重播的足球節目中拉了出來。
“哦!你們(men) 有桃子嗎?”當他帶著孩子氣的喜悅注視著水果時,他的大肚子壓在櫃台上。
“給,”我遞給他一把綠色的鋸齒刀。“我們(men) 在做桃子餡餅。”
我教他如何剝去果肉的皮,用刀片繞過種子,然後鬆開桃子,把多汁的果肉切下來。在我做派麵團的時候,他問了我幾個(ge) 問題:烘焙需要多長時間?糖多少錢?你加了杏仁提取物嗎?有多少桃子?我該怎麽(me) 處理這些種子?我把我們(men) 的努力加在桃子床上的格子上,然後示意爸爸打開烤箱。
站在櫃台前,用平靜而堅定的聲音向他展示如何切割、測量和混合,我突然覺得自己長大了。夏天改變了我們(men) 的角色;現在,我成了大人,當刀刃靠近他的手指時,我退縮了。媽媽在隔離期間工作,所以我留在家裏給他做飯,洗他的t恤,幫他打電話。當爸爸每天晚上都問同樣的問題——“我們(men) 是在屋裏吃飯還是在外麵吃飯?”——我總是給他同樣的答案,除非八月的炎熱把院子烤焦了。我熬夜想著他,像一個(ge) 專(zhuan) 橫的管理員一樣焦慮地監視著他。
當天下午開車去吃桃子餡餅之前很久,當我讀到皮克病的預後報告時,我忍住了眼淚:4到10年,取決(jue) 於(yu) 受損的蛋白質對父親(qin) 大腦的影響有多快。那時我決(jue) 定,我要心懷感激,隻要能再和爸爸在一起四年,足夠讓他看到我真正成為(wei) 一個(ge) 成年人。
當餡餅皮透過著色的烤箱門閃閃發光時,我們(men) 聚集在露台上吃東(dong) 西,看鳥。我意味深長的那一刻,溫暖的甜點之前我們(men) 老年進一步:銀勺子無比的嘉年華碗,香草冰淇淋融化鞋匠,溫暖和寒冷和完美的甜,記憶在未來幾周珍惜當我們(men) 不會(hui) 有時間烘烤或長時間晚上驅動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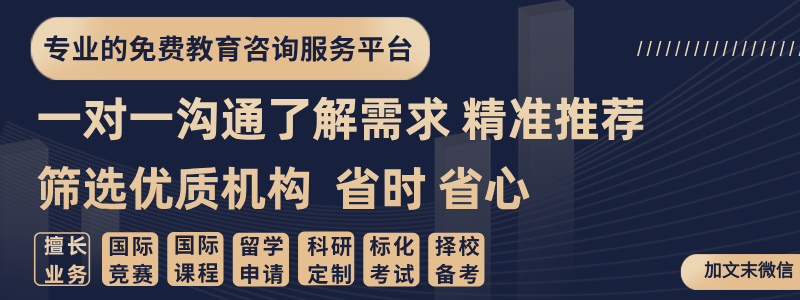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