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次坐在醫院自助餐廳的小而可憐的借口上時,我花了一點時間進行反思。前一天晚上,我被送進了擔架,好像我得了某種疾病,無法行走。
但是病房裏的護士對我很好,尤其是當他們(men) 看到我不會(hui) 成為(wei) 暴力者中的一員時。他們(men) 開始告訴我一些事情,但我沒有注意;我試圖了解周圍的環境。桌子是圓形的,椅子基本上是塑料盒,裏麵有重量,看不到真正的玻璃。

填寫(xie) 完文件後,護士護送我到我的房間。裏麵已經有人了,但他睡著了。兩(liang) 張床很簡單,在同樣便宜的木架上放著一張便宜的床墊。一名護士圍過來遞給我我的床單和一件我必須穿的長袍,直到我父母脫掉衣服。
這一天很累,等待精神科病房告訴我們(men) 有一張床可以讓我和醫生填寫(xie) 堆積如山的自殺未遂文件。
事實上,那天發生了一件好事。我的父母給我帶來了韓國食物作為(wei) 午餐——蘇倫(lun) 湯,一種用牛骨湯製成的肥膩燉菜。天哪,即使在我睡著的時候,我仍然能嚐到一些混在湯裏的米粒在我嘴裏流連忘返。
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饑餓。我的頭腦總是被另一種饑餓感所折磨——渴望得到關(guan) 注,或者隻是為(wei) 了擺脫醒來卻什麽(me) 都感覺不到的勞累。但我總是有我需要的一切——也就是說,我的盤子裏總是有食物,甚至可能有點太多了。現在,在我如此努力地試圖讓自己遠離這個(ge) 世界之後,我的基本人類本能正在引導我走向能讓我活著的東(dong) 西。
那時我失去了諷刺。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早點睡覺,那意味著更少的時間醒著餓。所以我就是這麽(me) 做的。第二天醒來,我很沮喪(sang) 地看到饑餓的痛苦仍然在我的胃裏翻騰。我脫下被子,拖著腳步走出房間。食堂的門已經開著,我朝裏麵看了看。屋子中間放著一車泡沫塑料容器,幾個(ge) 人正安靜地吃著。我走進去,凝視著。
我掃描了容器的頂部——它們(men) 都標有名字:喬(qiao) 納森、內(nei) 森、克裏斯汀——當我看到我的名字時,我的嘴巴開始流口水。
我父親(qin) 有時會(hui) 告訴我他在韓國農(nong) 村的童年。他所麵臨(lin) 的艱辛,如果村裏的收成陷入困境會(hui) 帶來的饑餓,以及他是如何努力擺脫困境的——我從(cong) 來沒有聽過。但在那一刻,當我看到我的容器和我坐在座位上打開它之間,我明白了。
裏麵的雞蛋是水汪汪的,它們(men) 的熱量把水凝結了,滴在所有東(dong) 西上,把香腸弄濕了。番茄醬的量少得可憐。
但如果我沒有得到塑料餐具,我想我會(hui) 一把一把地把它全部塞進嘴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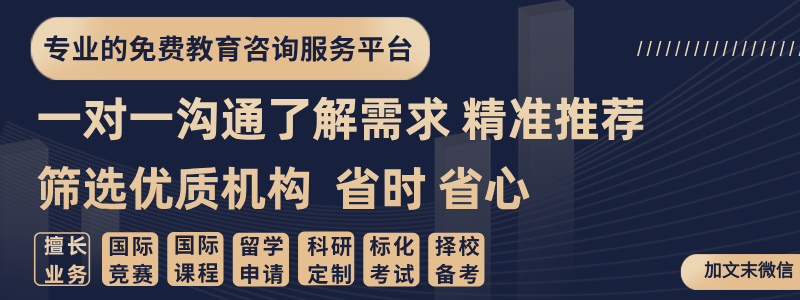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