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都是普通男孩:在學校努力學習(xi) ,在夏天度過每一分鍾,盡最大努力假裝我們(men) 對這個(ge) 世界沒有擔憂。事實並沒有什麽(me) 不同,因為(wei) 太陽在一個(ge) 溫暖的七月傍晚開始落山。山姆和我告別本,走出我們(men) 最好朋友的家。
“我們(men) 走路的時候姐姐會(hui) 來接我,可以嗎?” 我問。
“是的。”
“其實,她應該也可以開車送你回家。”
“聽起來不錯,”山姆說,但缺乏他一貫的樂(le) 觀和喜劇能量。我們(men) 倆(lia) 都沒有說別的,但我沒關(guan) 係,我們(men) 隻是繼續走。當溫暖的夏日微風拂過我的臉龐時,我環顧四周,欣賞著寧靜祥和的公園。蟋蟀在啁啾,一隻貓頭鷹在附近行駛的汽車輕柔的嗡嗡聲中歌唱。這是大自然的寧靜曲調。

我幾乎忘記了山姆和我在一起,直到他問:“我能問你一個(ge) 奇怪的問題嗎?”
“當然,”我說,像往常一樣期待一個(ge) 低俗的笑話。
“如果你不想回答,你就不必回答,”他在問之前說。
更猶豫的是,我說,“好的”
“你有沒有喜歡談論更深層次的東(dong) 西的人……喜歡更情緒化的東(dong) 西?” 沉默像一堵磚牆一樣擊中我們(men) :蟋蟀停止鳴叫,貓頭鷹停止鳴叫,甚至汽車也停止駛過。震耳欲聾。我隻是對這個(ge) 問題感到震驚,因為(wei) 它是山姆,我認識的最快樂(le) 和最有趣的人之一。
我在想。我的失望就像我的希望消失一樣迅速,因為(wei) 我沒有想出一個(ge) 名字。最後,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東(dong) 西是我在感到悲傷(shang) 或壓力時偶爾寫(xie) 的那本書(shu) 。
“嗯,”我平靜地說,“我從(cong) 來沒有真正想過這個(ge) ,但我想沒有。”
“是的,我也沒有,但在營地裏,我們(men) 開展了一些活動並進行了會(hui) 談,從(cong) 而引發了更多情緒化的對話。” 我默默地既嫉妒又為(wei) 他感到驕傲,但主要是嫉妒。
“這很有趣,”我說,“在英語中,我們(men) 總是開玩笑說那個(ge) TED Talk 的人談論人包廂,但它實際上是如此真實。我們(men) 不應該覺得我們(men) 不能談論更深層次的東(dong) 西。”
“是啊,”山姆笑著說。沉默再次籠罩著我們(men) ,但這一次更舒服。我迷失在我的思緒中,試圖思考接下來要說什麽(me) ,但是太多了。我以前從(cong) 未有過這樣的機會(hui) 。然而,它並不令人震驚或壓倒性的,即使它與(yu) 所有人中的 Sam 在一起——相反,它是治療性的。
Sam再次打破沉默:
“就像我從(cong) 來沒有告訴過你們(men) ,我的父母離婚了。”
“我——我很抱歉,”我說,“這真的很糟糕。” 我對自己沒有多說感到失望。
“沒關(guan) 係,”Sam 說,但我知道他在撒謊。我能感覺到他的悲傷(shang) 。
我沉浸在思緒中,試圖挑出一些話來。但是要說的太多了。沉寂16年,選擇太多了。
頭燈出現在我們(men) 麵前,一瞬間我鬆了口氣,但很快就變成了後悔。
知道是羅斯,我很快告訴山姆,“如果你想再說話,就告訴我。”
我向羅斯打招呼,用疲倦掩蓋了我莊重、深思熟慮的心情。和煦的微風給我的臉頰最後一吻;大自然恢複了她的號碼,當山姆和我不情願地踏上汽車時,汽車再次駛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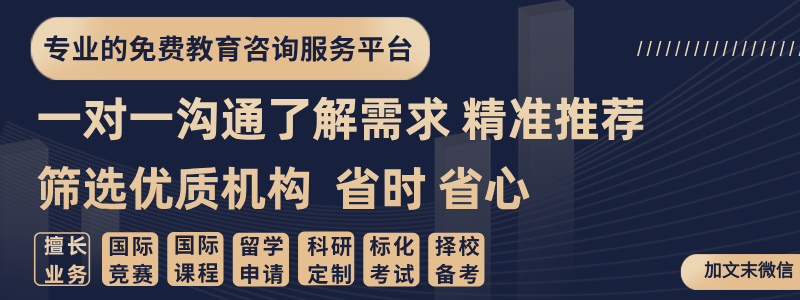












評論已經被關(guan) 閉。